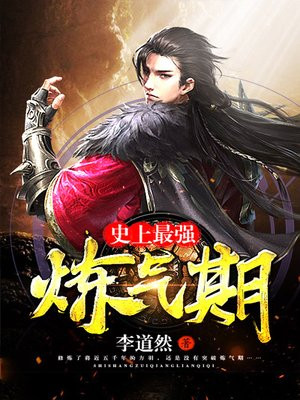冯谖很安静的看着白蝴蝶睡着的样子。她的眉头一直都是深深的锁着的,几乎要凝成了疙瘩,眼角的泪水一直没有停,所以泪痕一直都没有干。
冯谖知道白开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毕竟这是她的父亲。
一个人活着无非就是几个十年,开头的十年可以什么事情都不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感情便也愈发的丰富,当然也有人幼年丧父丧母的,可是他们未必能够有这般深切的疼痛。
就像冯谖,他爹死的时候才五六岁,那是个不懂得什么叫做悲伤的年龄,至于他深埋在心底的仇恨,说白了无非就是因为父亲死后所带来的种种困境让他萌生的。如果不是他爹被齐军杀死,他的母亲就不会因此而悲伤到双目失明,家族的长辈就不会如此不待见他们母子,他们就不会这么清苦。
是的,他对他的父亲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甚至连他父亲长什么样子都已经不记得了,可是这份仇恨是鲜活的,因为那段凄惨的时光深深的烙印在了他的心里。
更准确的说是他仇恨的是生活本身,而并非齐国趁着子之之乱在燕国烧杀抢掠,杀父之仇不过是根源,就像是种子,后面的生活才是适宜的空气、土壤、水分、温度。
但是白蝴蝶不是他。白蝴蝶的仇恨是切实的仇恨。这是真正的杀父之仇,与冯谖因为生活而滋长的仇恨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叹了口气,如果不是怕自己的轻举妄动吵醒了现在这个已经极度虚弱甚至于虚脱的美丽的女子,他真的会轻轻地抚摸着她病态的蜡黄色的脸颊。
狗不理几个人在后面静静的看着他,良久才道:“二师弟……”
冯谖回过头轻轻地道:“大师兄,我想再看看她,一个人静一静。”
狗不理点了点头,对着魏子风、郑良和刚进门的鸡鸣狗盗使了一个眼色,五个人都走了出去。百里玑也是个识相的人,她看得真真的,心里暗暗的叹了口气,不由得想如果自己当年真的选择了风嗣,是不是现在也能像眼前的这两个小辈一样美满?但是时间不会重来。
她也走了出去,带着满腔的惆怅感。
冯谖又缓缓的转过
了头,轻轻在弯下腰,将带着女人清新体香的棉被往上拉了拉,掖紧了,才坐在地上。他又叹了口气,不知该如何是好。
人越不知该做什么的时候越容易胡思乱想。
他在想白开,这个做爹的心机之重让人匪夷所思——要自己的女儿留在自己的身边做眼线,因为府上失窃便自己的亲生女儿吊打……这该说是家法森严还是别的?
白开心里是否有这个女儿冯谖揣测不来,但他能肯定的是,白蝴蝶的心中肯定是有她爹的。
冯谖舒出口气,两只手撑在地上,身子往后仰着看屋顶的房梁。他的眼睛空洞洞的没有焦点,累了就坐起来看白蝴蝶。
白蝴蝶真好看,细细的弯弯的眉毛,长长的睫毛,光滑的脑门,小巧的鼻子和嘴巴,薄而玲珑的耳朵……即使现在大病一场,这些美丽的东西依旧是美丽的。
冯谖轻轻地从被子里拉出她的手握着,这只手依旧是那么湿润、温暖、富有弹性,他不敢用力,生怕像小时候抓蝴蝶一样稍一使劲就将蝴蝶给捏死了。白蝴蝶不是真的蝴蝶,当然不会被捏死,但却会醒来,醒来之后呢?
冯谖握着这只美丽温暖的女人的手,不敢往下想。因为他知道,醒来了,梦也就醒了,哪怕是现在的片刻的宁静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他的右手轻轻地盖上了白蝴蝶的手背,两只手夹着白蝴蝶的手,一言不发的看着眼前的美人的睡相,总想要说点什么,哪怕对方听不见也无所谓。可是冯谖的嘴巴张了张,硬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日影渐渐西斜了,屋子里也渐渐暗淡了下去。冯谖没有去点灯,还是像一块石头一样握着白蝴蝶的手。
他这人思维是活跃的,平时在白蝴蝶面前也十分的能说会道,可是现在却哑巴了。白蝴蝶的心里乱糟糟的,他的心里也是乱糟糟的。
百里玑蹑手蹑脚的走了进来,也是一言不发的,点了灯,先看了看躺在另一张床上的郑袖。郑袖累了,还没有醒过来,她掖了掖被子,走到冯谖身后轻声说道:“谖儿,去吃饭吧!田文排了宴席……”
冯谖的话有些无力和缥缈,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一样,他道:“我不饿…
…”
百里玑叹息道:“就算不饿,好歹也吃一点吧!不吃饭怎么行呢?”
冯谖沉默着,又变成了石头。现在的他根本就无心吃饭,如果她去参加宴席,郁郁不乐的弄不好大家都没了胃口。百里玑也不说话,只是悲伤而且沉痛的看着这个后辈的身影,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前的风嗣。
只是风嗣总是能够笑着的,而冯谖现在没精打采。
百里玑站了很久,见冯谖没有起身的意思,她终于放弃了,在长叹一声之后,转身出了屋。
冯谖的脸还是像磐石一样没有一点变化,只是静静地看着还在沉睡的白蝴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冯谖轻握住她的手使她心里有了些倚靠,还是因为明白冯谖也在随着她一起悲伤痛苦,总之,她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