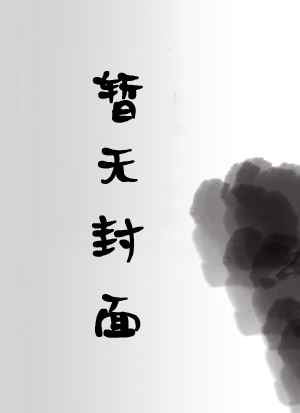簇山东面,大泽之畔。
余天万矗立巨石之上,遥望浩渺烟波,心中坚硬如铁。
“余师兄,元敬在哪?对付奇虫,还需他出力!”金天武站在余天万的身后,忍不住问道。
余天万侧首反问道:“若无元敬那件奇宝,我们便不敢与敌一战吗?”
金天武摇头:“非也。奇虫虽诡谲邪异,但我们也有手段可制。只是,毕竟是数十人出战,混乱之中,难以顾全,若是损伤过多,不免至于溃散,反给敌人可乘之机。”
余天万知道他担忧什么,却毫不避讳,直言说道:“金师弟此言差矣。天魔渊多年征战,嫡系的结丹修士也没几个。此次前来阻击,半数皆为附庸。此等修士,不过见风使舵,形势不利,溃逃起来比我宗下宗修士更加不堪。此战的关键,还在于我辈,若是我辈不惧伤亡,与敌血战到底,下宗修士又岂会轻易溃散。诸般手段、物品,不要吝啬,该用就用,打赢此战,宗中局面必定会大为改观!”
金天武略显尴尬,欲言又止,终究归于沉默。
站在巨岩之下的下宗修士,无疑都把余天万之话听得清清楚楚,一个个面色复杂,不知在想着什么,但无人出言说话。
反倒是站在金天武身边的郑天佑,愤愤说道:“余师兄,我等为宗门出战,当然全力以赴,再所不惜。只是,事先定计,便是要引敌会战,然后趁敌自以为得计之时,以元敬之奇宝扭转局面,从而大破对手。现在,敌人已来,诸事皆备,为何元敬却失约不至,此何意也?岂非视宗中大局如儿戏!”
余天万严肃地看着他,厉声说道:“郑师弟,慎言!元敬不至,乃是真人有命。此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西方,在玄元殿那里。我等便是拼得血流成河,也要拿下此战,绝不能怀着侥幸心理,想着轻松获胜。对方乃是有根脚的大势力,不是乌合之众,若我们没有拼命的准备,此战堪忧!”
郑天佑很少见余天万这般严厉地训斥,不敢再言,讷讷退下。
余天万转动目光,看向巨岩之上的一众玄天宗结丹修士——金天武、闵天卓、谷天啸、郑天佑、游天梧,以及受真人之命前来支援的孙天翼、何天鸿、施天翰、陶天兴、姜天浩,掷地有声地说道:
“诸事自有真人运筹帷幄。我等,唯需勠力同心、全力出战。诸位师弟要牢记,此非修道人之间的斗法争胜,而是关乎宗门存亡的生死之战,来不得半点轻忽和侥幸,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我们没有选择,没有退路,只能死战到底!”
随后,他上前几步,分开玄天众结丹,走到巨岩边缘,对着下方的下宗修士说道:“诸位,天魔渊之部署,我已尽知矣。他们此来之人,不过二十余人,比我方要少出近十人。是他们人手不足?非也。
“他们集聚于簇山中的结丹修士,少说也有近四十人。为何只来半数?因为要诱我等入陷阱。他们在簇山核心之地,设有一处大阵,内中伏藏数万妖禽,只待将我等引入阵中,便可一举歼灭。
“我等既知此计,胜敌自不待言!此战,我玄天宗诸结丹将冲锋在前,以朱雀阵向敌部发起决死冲击,你等跟随在后即可。若我这朱雀阵敌不过对方,你等自可离去,以全性命,无需死战!”
下宗修士先是一阵沉默,随即,便有一人喊道:“余长老,天魔渊贼子欺人太甚,我等早已不堪忍受,此战必得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将他们逐回老巢去!”
此人名马杰,乃是衍灵宗此代掌门,须发皆白,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在玄天宗下宗修士中多有令名。
天符宗的崔怀远立即出声附和:“马宗主说得好,就要杀天魔渊一个片甲不留,好叫这些宵小之辈知晓,天阙山不是他们撒野的地方!”
能够听从玄天宗号令征讨天魔渊据点的下宗修士,无疑都是铁了心要与玄天宗一条道走到底的。
故此,众人也纷纷出言表态,愿意跟随余长老和玄天宗众长老一起,同进退、共存亡。
“多谢诸位!此战之后,我玄天宗必有重赏!”余天万振臂高呼,“走,且随我去会一会天魔渊众修!”
余天万纵剑在空,玄天宗诸长老紧随其后,渐次摆开位置,形成朱雀之阵。
玄天宗四大基础阵法,白虎之阵强绝,一往无前,不死不休;青龙之阵,攻守平衡,用力绵长;玄武之阵,防中有攻,坚如磐石;而朱雀之阵,分合由心,因势成形,最擅长因应变化,常用于遭遇之战。
诸下宗结丹,肃容跟上。
自天魔渊侵袭玄天宗以来,两宗之间,双方各出数十结丹修士进行大战的次数,屈指可数,且均在开战之初,近几十年来,双方在流云城附近鏖战,多是小规模战斗,少有超过十人之数者。
在大泽的另一侧,齐旭阳负手而立,远眺西方诸峰。
身材干瘦、容貌苍老的曲泽站在他的身后,问道:“齐师兄担心簇山那边?凌长老虽然年轻,但自幼被凌真人收在身边调教,见多识广,气度非凡。尤其是凌真人意外陨落后,他变得更加沉稳,凡事思虑入微、推敲周全,又有大阵为依,必无差错。”齐旭阳摇摇头:“我不是担心他不够细致,而是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