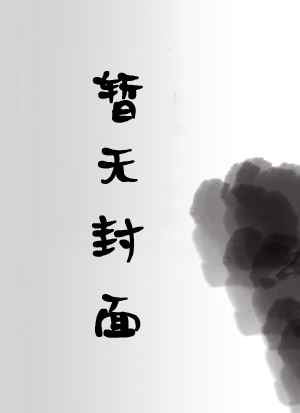杜素清颤颤巍巍的起身,指着闯进来的大理寺官兵问道:“吾乃朝廷命官,尔等居然擅自闯入我的府邸。”
黄正启一身朱红的官袍,进门后对着杜素清拱手道,“奉陛下手谕,前来查案。”
杜素清坐了回去,不停的咳嗽。
“鹤鸣山一事,坍塌乃天雷所致,此事毋庸置疑,不仅老臣,叶大人,还有宫里的两位娘娘以及山上的侍卫宫人都可以作证。”
黄正启看着眼前双颊凹陷、面色出现不正常的潮红官员,摇了摇头说道:“今日下官前来,是来查另外的案子,还请大人配合。”
“何事?”黄正启在下人的搀扶下喝了口水,靠坐在床上说道。
“昨夜三位御史大人皆在睡梦中被人杀死,其中童大人昨日曾到大人府上拜访,是与不是?”黄正启一边询问,一边紧紧盯着他。
杜素清皱着眉头思索了片刻,“这些日子身体都不利索,昨日只有户部的叶怀昭叶大人,进来陪着我坐了一会儿,其余来探病的人,都被我回绝了,你可以去问问管家,管家应当记得童大人有没有来过。”
管家在迎他们进门的时候就已说过,大人素来与童大人没有交情,因此便被管家以大人昏睡给拒了,但黄正启显然并不相信。
“大人,此事涉及到当朝官员,人命关天,大人,在下得罪了。”
说完对着黄正启一抱拳,又对着门外的衙役吩咐道:“你们到其他的地方仔细搜一搜,注意不要打扰到杜大人的家人。”
“你们要干什么?”屋外响起了管家的怒斥声。
“得罪了!”
说完黄正启便在杜素清的屋内开始了翻找,丝毫不理会杜素清在身后的怒斥。
杜素清的屋子里,有大量的书籍,并且堆放的到处都是,黄正启背对着众人,重点翻找着其中的书信。
他神情专注,一目十行,慢慢的嘴角带出了一丝笑意。
他将手中的书信塞入了袖中,大步向外走去,示意守在门口的衙役,“守在此处,不许任何人出入。”
杜素清看着他的背影,心中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种预感从他接手皇泽观修筑一事就隐隐存在,而此刻他心中这种预感已经到达了顶峰,幸好,他已经让杜雨赶赴豫州,将他的口信带给了唯一的儿子,有了亲家的庇护,保全自己问题不大,希望自己的家仆不要受到过多牵连吧。
“此信乃是在杜素清的卧房隐秘处搜出,乃是一封密信,信中所记载的事情,正与鹤鸣山出事那夜一致。”黄正启对恒昌帝禀告着。
“杜爱卿,你可有话要说。”恒昌帝不怒自威,目光烁烁的盯着瘫倒在地上的杜素清。
“老臣是被冤枉的,我从未见过此信。”杜素清只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哽住,他看着那信上陌生的字迹,知道这次自己是难以脱身了。
“陛下,臣一生尽忠职守,殚精竭虑,从未以权谋私,不结党不营私,陛下,您应当是看在眼里的啊,此次分明是有人可以栽赃陷害,请皇上明察,不要被奸人所蒙蔽啊。”杜素清几日下来,看上去竟然比往常老了十岁,恒昌帝看的也有些不忍。
“陛下,臣与杜大人虽相处时日尚短,日常相处中也对杜大人为人知晓一二,实在不像是能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事情的人。”叶怀昭温言对恒昌帝说道。
“再说了,若真是有人与杜大人勾结,这封信应当早就被毁掉了,何必还藏在家中等着被抓现行?还有那日鹤鸣山忽然天降大雨,怀昭也在山上,白日里晴空万里,夜间却忽然变了天,杜大人如何提前能得知呢?”叶怀昭不忍看他成为此事的替罪羊,替其分辩道。
杨景修也站出来:“父皇,杜大人脾气直,遇到事情一向直言不讳不知变通,说不定是在什么时候得罪了人而不知,被人故意陷害也不可知。”
“禀陛下,我们搜查了杜大人家中,不知杜大人家中,有两名从小养大,视作半子的杜风杜雨何在?”黄正启咄咄逼人的问道。
“据我所知,此二人乃是杜大人的同族远亲,一般跟随杜大人做事,据杜家仆人交代,杜风在一月之前离京,杜雨在三日前离京不知所踪,杜大人,他们究竟去为你办何事去了?”
杜素清只得苦笑一声,两人皆是去了豫州,找自己儿子去了,但此时若言明,那之前儿子所绘图纸一事必然瞒不住,又会将亲家牵扯进来。但他的表情看在恒昌帝眼中,便是有意隐瞒。
“杜雨刚刚离京,我已传信各大驿站,一露面便将其捉拿,如今已经在押解回京的路上的了。”
叶怀昭眼神却一变,杜雨绝对不能被他们抓到,他设计雨夜趁乱劫走黄金一事,除了白起瑞的人,便只有杜雨知晓,若是杜雨熬不住审讯,将他供了出来,那他便功亏一篑了。
杜素清却笑了起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叶怀昭好言劝道:“杜大人,如今此案由陛下亲自审理,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你说那封信是被栽赃,不如好好的想一想,可能会栽赃的人。”说完眼神轻轻的瞟了一眼黄正启,提醒他,那封信很有可能是黄正启自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