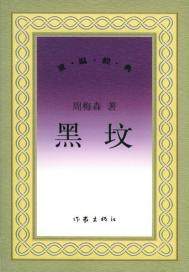古黄河大堤像一条连绵起伏看不见首尾的巨大的长龙,静静地伏卧在这块浸透血泪的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它高大而又陡峭,对着旷野和涌着河水的两面斜坡上长满了青绿的野草、野蒺藜、酸枣树棵子,很有些生机勃勃的样子。堤埂很宽,可以走得牛车、驴车、独轮车,在当地人们的习惯意识中,素来是一条通衢大道——至少依傍着田家铺的这一段是这样。大堤由砂礓、黄泥构成的,堤面上嵌着两道深深的车辙沟,像大华公司为运煤小火车铺设的铁轨似的,这车辙沟里,晴天沸沸扬扬地腾着浮土,雨天满满溢溢地积满泥水,终年如此,仿佛它们要和这古黄河大堤一起,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历史遗迹,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大堤下,原本是一片空旷的生荒地,生荒地上是一片乱坟岗子,素常没有人烟,当年曾文正公跑马划地,划出的尽头便是这里。胡、田两家的分界堤——也就是现在的分界街,也合乎情理地修到了这大堤下面。开矿以后,这里才渐渐热闹起来,没有坟主的乱坟岗子被逐渐铲平了,一座座、一片片土庵子、草棚子、茅屋子建起来了,大华公司开矿挖出来的矸石碴也开始堆到了这段大堤的护坡上。于是,这条用黄色的泥土,用大地的精灵,用几代人的心血建筑起来的大堤上,出现了一段刺目的、灰褐色的地段,使那些看惯了黄土,看惯了这条大堤本来面目的人们很不舒服。
田二老爷便是其中的一个。
田二老爷每每看到这段灰褐色的堤埂,总免不了要想起可恶的大华公司、总免不了要在心里诅咒几句。
现在,二老爷心情极为恶劣,二老爷恨呵,尤其看到这来自深深地下的灰褐色的矸石,更觉着十二分的不舒服。二老爷固执地认为,田家铺目前所面临的一切危难,他面前所出现的一切难题,都是大华公司一手造成的!就是田老八杀人,也是大华公司造成的!二老爷懂逻辑,二老爷的逻辑是:倘或大华公司不到田家铺开矿,则不会出现五月二十一日的矿难;倘或没有五月二十一日的矿难,《民心报》记者刘易华则不会到田家铺来,而刘易华不来,田老八也就不会杀人!
罪恶之根源还在于大华公司的开矿!
然而,二老爷严以律己。罪恶之根源在于大华公司,可二老爷要严以律己。二老爷就是这么高尚。二老爷由刘易华的被杀,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嘴上不说,他心里承认,他是有责任的,田家的族人中出现了田老八这么一个无情无义、出卖朋友、认贼作父的不孝子孙,不能不是田家门庭的耻辱!作为一族之长,他至少得认这么一个账:他管教无方……
镇上的窑民们将田老八抓住,五花大绑地押到他府上时,他呆住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田老八会为着一百五十块大洋,去杀掉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省城记者!他顿时觉得无地自容,他甩手打了田老八两记耳光,吩咐手下的人将他关到磨房里去。
窑民们不干,领头的两个客籍窑民坚持要将田老八立即处死。
他生气了,他觉着这是对他的不信任,这是对田家门庭的蔑视,好像他们料定他田二老爷会徇私情似的!
他冷冷地对窑民们道:
『该咋处置这个畜生,你们不要管。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田家乃世代仁义之家,二老爷我会给他动动家法的!倘或我处置不公,你们再找我理论就是!』
『好!二老爷,我们听您的,可有一句话我们要说,杀人是要偿命的!若是我们在田家铺镇上再看到这个王八蛋,甭怪我们对您二老爷不敬!』一个客籍窑工硬硬地道。
二老爷火了。这帮臭窑民凭什么用这种口气和他讲话?他几乎要发作了,可咬咬牙还是忍住了,他觉得自己输理了。他们田家门下出了这么一个败类,他还如何硬得起来?!
真丢人!
真丢人呀!
窑民们一走,二老爷便将自己独自一人关在屋里。二老爷是仁慈的,他不想杀掉田老八,他千方百计想为田老八杀害刘易华找一点理由。他想,只要能找到一点稍稍站得住脚的理由,他都可以不杀他,然而,最终他还是没找到。他将田老八押到面前来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田老八就是为了钱,就是为了那一百五十块大洋!这使得二老爷痛苦万分,二老爷极敏感地想到:今日里田老八为了一百五十块大洋可以杀掉刘易华,日后,势必也会为着一百五十块大洋,或者一千五百块大洋杀掉他田东阳的!这种孽种留下来,不但辱没田家门庭,也会祸害地方乡民,留下他,就是留下了一条祸根!而且,为此还会得罪那些客籍窑民,涣散他们的斗志,使得他们和他离心离德,那这场战争也就无法打下去了。
自然,二老爷也不喜欢刘易华。二老爷后来还是听说了,幕后挑唆田大闹他们闹独立的,就是这个刘易华!这个刘易华实在是太狂妄了。前些日子,二老爷还想利用这个刘易华,为田家铺民众,为田家铺进行的这场战争造一造舆论,谁料想,他不但与张贵新为敌、与大华公司为敌、与北京**为敌,居然也和他田二老爷为敌!刘易华压根儿不是个东西!他从省城跑到田家铺来,也是别有用心的!他不承认任何权威,根本不把他田二老爷看在眼里,现在死了,也是一种报应!他想,设若田老八不是为了一百五十块大洋,而是为了刘易华对他田二老爷的不敬去杀了他,那他会宽恕他的,哪怕担点风险,他也会宽恕他的——至少,他可以偷偷把他放走,让他到外面混世界去。
现在却不行!他是为了一百五十块大洋,而不是为了仁义;他杀了人,就得偿命!而且,从大道理上讲——暂且抛开刘易华对他田二老爷的不敬,刘易华到田家铺来,还是向着田家铺窑民的,他是站在窑民一边,反对公司、反对大兵的。就冲着这一点,不杀了田老八也说不过去,人家会骂他田二老爷徇私情,不仁义!
二老爷决定做一个仁义的族长。
二老爷决定杀掉田老八。
当晚便找来了田家有头有脸的老少爷儿们,商讨对田老八的处置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人替田老八说情——二老爷决定杀,谁还敢替他说情?!
于是,便定下来了:背石投河。
于是,今日傍晚,二老爷带着一帮族人押着田老八,鸣锣穿过喧闹的西窑户铺街面,来到了古黄河大堤的堤埂上。
于是,在崇高的、神圣的、古老的仁义道德的支配下,一个古老宗族的严正家法付诸实施了——
灰褐色的堤埂上挤满了人,堤埂下的旷野上也滚动着一片片人头,人头的空隙中竖着一杆杆飘着红缨的枪头子和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大刀片。田氏家族的年轻汉子们手执刀棍在二老爷一行人周围组成了一道严密的警戒线,阻止任何人涌入线内。站在堤埂两旁的人们开始时骚乱了一番,想往线内挤,后来发现无法挤进去,也就作罢了,一个个用石块垫高脚站在远处看。
杀人毕竟是一件十分好看的事,不管是官府杀人,还是民间杀人,总是很好看的。眼见着一个活生生的性命在一瞬间像烟一样地骤然消失,活着的、围观的人就会产生一种非凡的满足,哪怕是身无分文的人,也会感到这种满足,至少他们会认为,他们还活着,他们要比这死去的人强得多!
今天是你,以后才轮到我呢!
就凭着这一点,活着的人们,也就有理由十二万分的高兴和自豪了。
田老八被五花大绑着,由两个田姓乡民押上了大堤,押到田二老爷面前跪下了。田二老爷身后是一乘竹子凉轿,凉轿旁边是半截沉重的磨盘。二老爷手托着水烟袋站在大堤上,面部毫无表情,他仿佛在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对着古老的黄河遗迹,思索着关于人类道德的重大问题!
风很大,二老爷的衣袖、裤腿,二老爷那花白的头发,全被迎面吹来的风撩到了身后。二老爷很威严,他似乎不是在处置一个败坏了门风的族人,倒像是要审判天地似的。挤在最前面的人们看到了二老爷眼角上的泪。
在田老八被强按着跪在砂礓地上之后,二老爷眼望着高远的天空,缓缓说话了,声音苍老而悲切:
『老八,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我……』
二老爷转过脸去,依然不用正眼去瞧田老八,两眼依然看着天,可他实实在在是准备听田老八的遗言的,他面孔上松垮的肌肉在微微颤动。
田老八却没说下去。
二老爷终于低下了头,冷冷地看了田老八一眼,看他的时候,二老爷左眼角的一滴泪滚了下来。
二老爷不经意地将它抹去了。
『说吧,老八!再晚,就没时间了。』
『我……我……』
田老八突然挣扎起来,他两眼盯着二老爷,要往二老爷脚下扑。可他没有成功,两个看押他的人将他按倒在地上了。
他趴在地上骂:
『二老爷……田……田东阳,我操你祖宗十八代!我……我恨你这个老王八蛋!你为富不仁,你欺压族里爷们,你这老王八蛋不得好死!』
有人冲上去堵他的嘴。
二老爷抬抬手,将那人阻止住了。
二老爷宽宏大量:
『你,你接着说!不要光骂!你说说看,二老爷我如何为富不仁?如何欺压族里的爷们?说吧,别把肚里的话带走了!』
二老爷平静而坦然,他料定田老八讲不出什么来!
田老八自知死罪不可免,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又趴在地上喊道:
『我……我田老八杀人是你这个老王八蛋逼的!你夺走了我的地,逼着我卖了牛,你想把我从我的地里赶出去,让我去下窑,去送死!我不!我偏不!我杀刘先生是为了还你的债!是你唆使我杀的!迟早有一天,咱田家的族人们也得要把你背石沉河……』
二老爷听着,痛苦地摇着头,直到田老八喊完了,才不动声色地开口道:
『老八,民国三年,你借没借我的钱?借钱该不该还?你还不起钱,我到你家揭过锅、扒过灶么?地是你典给我的,还是我田东阳夺走的?人,说话得凭良心!不凭良心,连狗都不如!我再问你,难道你为还我的钱,就非杀人不可么?就是要杀人,你也不该杀刘先生,你可以杀我嘛!杀了我,这债不就勾销了么?!』
『你假仁假义,是他妈的笑面虎!』
二老爷长长叹了口气:
『看看,又骂上了!又骂上了!有理你就讲么!骂什么呢?明白地告诉你,你今日就是再骂再嚼,也难逃一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古今一理!我田东阳不能为了保你一条狗命,不要列祖列宗、不要咱田家的世代仁义!我不怕你现在骂我,也不怕你到阴曹地府骂我,我田东阳人正不怕影子歪,你骂也是骂不倒的!现在,我倒劝你想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甭到了那边又后悔!』
这时,人群里挤出了一个蓬头散发的女人来,这女人不要命地扑到二老爷面前,抱住二老爷的腿就哭:
『二……二老爷,您老发发善心,饶……饶了老八吧!老八不是人,老八是一时鬼迷了心窍!二老爷,您……您剁了他的手!您砍了他的腿,可您留他一条命吧!他上有七十的老娘,下有我们这些孤儿寡妇!二老爷……二老爷,您……您老人家就饶了他这一回吧!让他给您老当牛、当马、当狗,您……您饶了他一条命吧!』
二老爷命人将那女人扶起。
那女人不起,依然抱着二老爷的腿,趴在二老爷的脚面上哭:
『二老爷!二老爷!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老八好歹是田家的人……』
二老爷眼眶里聚满了泪。
二老爷亲自弯下腰,用颤巍巍的手去扶那女人。
那女人不起来,那女人对着二老爷一个劲地磕头,头磕在地上咚咚地响,额头上磕出了血!
『二……二老爷,您……您老人家不答应我,我不起来!』
二老爷没办法了。
二老爷仰面长叹一声,眼眶中的泪流了出来,他任凭泪水在那宽大的脸上流着,固执而严正地道:
『我不能徇私情!不能!咱田家门下祖祖辈辈没出过这种见利忘义的人!我留着他这一条性命,上逆天理,下犯家法,田家铺的兄弟爷们得指着脊梁骨骂我!我……我不能,不能这样做!』
田老八又叫了起来:
『毛他娘,别求这个老王八!别求他!他是个为富不仁的东西!你没有钱,他就六亲不认!别去求他了!你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别在这老狗面前跪着!穷要穷得有个志气!别像我,去杀那无辜的人!以后要杀就杀这条老狗!』
二老爷恍惚没听见田老八的叫喊,他依然低着头对田老八的媳妇说:
『我不怕你恨我,我实在没办法,我得按咱们田家的规矩办事……』
『可二老爷……二老爷……老八去了,我们这老少三代可怎么活呀?二老爷,二老爷,您老人家行行好吧!』
二老爷极和气,极恳切地道:
『不怕!不怕!老八去了,还有大家伙哩!老八典给我的那块地,我还你;老八欠我的账,我一笔勾销!行么?若是日子还过不下去,你们就来找二老爷我,有二老爷我一口干的,就少不了你们娘们一口稀的!二老爷我说话是算数的!』
二老爷说这话的声音不大,二老爷不是假仁假义的人,二老爷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可二老爷身边的人们还是听见了,人们无不为二老爷宽广而仁慈的胸怀所感动,拥挤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片赞叹之声。
『二老爷,唉!唉!二老爷哟……』
『仁义!这才叫仁义哩!』
『看他老八还有什么话说!』
…………
围观的人们啧啧议论的时候,一个田家的长辈远远地叫了起来:
『老八,你亏心不?你还真有脸活下去?你个混账东西还不向二老爷认个错?』
田老八的心也被二老爷的一席话打动了。这是他没想到的!他做梦也想不到二老爷会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场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答应还他的地,答应免他的债!这就是说,他田老八死了,他的老婆孩子还可以像模像样地活下去!这就是说,他的三个儿子都不会被逼到地层下去了!天哪,竟有这等事!二老爷竟然这么大度、这么有气量,竟把他身后的事情安排得这么合情合理,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是该死的,他一时糊涂,上了那个大兵营长的当,杀了人,干了不仁不义的事,这怪不得二老爷的,二老爷不杀他,那些客籍窑民也会杀他的!
原来,原来并不是田二老爷要杀他呀!
他错怪了一个多好的人呵!
他混账,他真混账!
他愧疚而又恐惧地哭了。
他冲着二老爷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声音哽咽着,说出了一句真诚的话:
『二……二老爷,我……我错了!』
二老爷庄重地点了点头,缓缓地道:
『知错就好……就好!二老爷我不怪罪你!你也甭记恨二老爷我,我……我……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二老爷不忍再说下去了,手一挥,示意押解的人执行背石沉河的家法。
两个家人抬着那半截沉重的磨盘压到了田老八的脊背上,磨盘孔上系好了绳子,绳子在田老八的脖子上绕了两圈,扎成一个死结,剩下的一截塞到了田老八的胳肢窝里。
田老八被压在地上软软地跪着,头垂得很低,几乎碰到了长满野草的地面。
二老爷又挥了挥手,四个人抬起了背着破磨盘的田老八走下了大堤。
在往大堤下走时,田老八本能地挣扎起来,可他没有骂。在挣扎的时候,半截磨盘从背上滑落下来,死死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勒得他直翻白眼。
『扑通』一声,他被四个人提着胳膊,提着腿,甩进了河里,甩得不太远,他落水的地方离河沿只有五六步。
这显然是很让人失望。
田老八被扔进河里后,便再也没冒上来,离得近的人说是看到了他的脚,说他的脚曾在河面上出现过两次,把河水蹬出了一圈圈新的波纹。大多数人却没有看到。那些对看杀人有着极大兴趣的人们,无不感到极大的失望,他们原来以为大名鼎鼎的『背石沉河』十分地好看,现在看了一回,也不过如此么!
他们一致认为,『背石沉河』还不如杀猪更耐看。
围观的人们带着各自的失望,纷纷散开去。二老爷也坐上凉轿顺着大堤往分界街上走了。田老八的媳妇哭昏了过去,二老爷临走前也并没忘记留人照料她……
很好。
一切都很好。
古黄河大堤还像巨龙一样静静伏卧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河中的水还在静静地向着那千古不变的方向流淌,血红的残阳依然高悬在远远的天际,旷野上的风依然带着泥土的腥湿味在田家铺周围的土地上飘荡着……
仅仅是死了一个应该死去的人。
田二老爷不后悔。田二老爷在古老的仁义面前,在这块土地朴素而又简单的真理面前,显示了自己无可非议的高尚与公正。
当四面八方的枪声再一次稀落下来的时候,大华公司总经理李士诚带着两个身着便衣、揣着短枪的矿警,沿着公司公事大楼的墙根,溜到了外护矿河边上,通过护矿河上临时架起的木桥,逃到了公司生活区外面。
这时,那轮血红的残阳已沉到了遥远的地平线下,西方的天际上抹满了橙红色的斑驳的云霞,广阔的原野上升腾起袅袅飘浮的轻纱般的湿雾,那湿雾和田家铺镇子上空的炊烟混杂在一起,一阵阵向高远的夜空中飘散。枪声停了下来,依傍在古黄河大堤下面的田家铺镇和田家铺矿区显得出奇的宁静,仿佛这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灾变,根本没有进行战争似的。顺着公司挖掘的排洪沟走到大堤上时,李士诚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像一条摆脱了旋涡恶流缠绕的鱼儿一样,再一次领略到了自由轻松的滋味,他突然觉着,不论在任何时候,活着,都不是一种负担。
黄河故道大堤上那一幕执行家法的壮剧已经演完,该死的,死去了;该走的,走掉了;连哭昏在大堤上的田老八的媳妇,也被田家的女人扶回去了。没有什么人留在大堤上,连绵起伏的大堤像一道森严而又破败的城墙,拥着一河清波,从看不到尽头的遥远天边伸展到李士诚脚下。他心里很坦然,他也没感到害怕,他并不知道在这道森严的大堤上刚刚执行过一个罪犯的死刑。他穿着皮鞋的脚板击打着这段灰褐色的大堤时,夜幕已在飘渺的轻烟中挂落下来,正前方墨蓝色的空中已隐约现出三五颗星星,他有了一种安全感,他想,他只要悄然通过这段大堤,就可以穿插到旷野的小路上,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今日下半夜——最迟明日一早,赶到宁阳县城。下一步,他就可以逃到天津,或者上海……
他这样做并不是不负责任,他愿意负责任,愿意承担起一切应该由他承担的责任,他愿意接受**的公道裁决,但却不能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压榨与欺辱!战争并不是他挑起的,战争的恶果,也就不应该由他一个人独吞!他曾经同意封井,但他不希望以这种流血的、武力的形式解决窑民的骚乱问题,他甚至宁可向窑民们作出更大的让步,也不希望进行这场战争。不错,窑民们太蛮横,太不讲理,窑民们截击了北京的委员团、占住了矿区、阻止了**的封井计划,可这也不能打呀!打到最后,张贵新和他的大兵一走了之,这残败的局面他如何收拾?大华公司还要不要办下去?他是实业家,不是军事家,他要的是煤炭,要的是钱,而不是窑民们的尸体!
在战争爆发之前,他通过县知事张赫然,三番五次劝张贵新,请他不要打,张贵新却不听。张贵新要面子,张贵新要在窑民们身上找补回他在委员老爷们面前丢掉的面子,张贵新要打!他曾经答应捐一万块大洋的军饷给他,但他还是要打!当时,实业厅的矿务专办李炳池也在一旁以威胁的口吻提醒说:地下大火在蔓延,如果再不封井,田家铺煤田就完了!他也只好让他打——不管他如何阻拦,人家还是要打的!他的命运从五月二十一日的大爆炸开始,已不是他自己能掌握的了。
他也恨那些无赖的窑民,事情闹到今日这一步,完全是窑民们造成的!这些窑民根本不讲道理,不顾大局,甚至动枪、动炮,再三滋事挑衅,这才最后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开初,他尽管提心吊胆、心魂不定,可还是认为窑民们是不经打的,少则半天,多则一天,战争就会顺利结束,窑民们就得抛下一具具尸体,狼狈逃出矿去。却又不料,窑民们竟打得十分顽强,鬼也搞不清他们从哪儿搞来了这么多钢枪、这么多子弹,从六月四日到六月六日,硬是和张贵新两个团的大兵整整对峙了三天,竟搞得这两个团的大兵毫无办法!张贵新连着三天未能攻进矿内,情绪变得极为烦躁,张口就骂人,不但骂他的部下,居然也骂起他李士诚!骂他不该修护矿河,不该筑高墙,不该把矿门建得像城堡,好像战事失利的责任也该由他李士诚来负似的!
协理陈向宇是聪明的,他劝他早一点离开矿区,先到县城,和那帮逗留在县城的**委员团的委员们谈谈,做些疏通工作;尔后,到天津和上海去,通过关系打通北京**的各个关节,准备处理善后问题。他想了想,认为这是可行的,遂将离开矿区的打算告诉了张贵新。张贵新一听就火了,拍桌子砸板凳的又是一场恶骂:
『妈的!你姓李的也要跑?你往哪里跑?!噢,刘芸林跑了,张赫然跑了,你们都他妈的跑了,想留下老子在这里给你们擦屁股?你他妈的想得美!老实告诉你!我姓张的不走,你狗日的也走不了!弟兄们是在给你卖命,军饷你得出、粮草你得管、死人你得葬、活人你得养!你他妈的敢跑,老子就叫底下的弟兄冲着你的脑门练枪法!』
当时,他真有点按捺不住了,他真想痛痛快快地用最恶毒的语言和张贵新对骂一通,他觉着他的人格、他的尊严受到了污辱。
然而他不敢。他的好时光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爆炸之前已经过完了,他在张贵新面前已不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实业家,而不过是一个败得一塌糊涂的上流乞丐。
可他还是说话了,他不卑不亢地道:
『张旅长,我并不是要逃走,也不是对您和您的弟兄们不管不问,我走了,赵副总经理还在,陈协理还在么。一切,他们会负责的!再说,上海、天津,也是中华民国的地盘么……』
张贵新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
『别他妈的给老子玩花招!上海、天津是中华民国的地盘,可他妈的不是老子的地盘!老子就要你呆在宁阳,呆在田家铺!』
他简直被张贵新的蛮横气昏了,愤然反驳道:
『我愿意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在**的公断下来之前,我有我的自由!』
张贵新拔出手枪,『啪』地拍在桌子上:
『你有自由,老子有枪!老子一枪就能毙掉你八个自由!』
恰在这时,陈向宇走进了屋子,他显然在门外已听到了他们的争吵,一进屋便劝道:
『二位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李公,您少说两句;张旅长你也消消气,李公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现在外面四处都是窑工,哪里跑得出去呢……』
在陈向宇的劝解下,一场小小的风波才告平息。
这是今日上午的事。
傍晚,陈向宇悄悄跑来找他了,并给他带来了两个换上了便衣的矿警。他自己也做好了出走的准备,十几根救急的金条已缠裹好,扎在了腰间,一件七成新、不太显眼的灰绸子长袍也从箱子里找出来,穿在了身上。陈向宇将他送到了护矿河边上。临别时,他握住陈向宇的手,眼里落下了泪,悲切地对陈向宇道:
『向宇,我走了,这里全拜托给你了,老赵无能,一切还劳你多费心,你今日为大华公司所作的一切,我李某都铭记在心,只要能躲过这次大难,我……我一定要加倍报答你的!』
陈向宇也动了感情:
『李公,不要这么说,这一切都是我该做的,谈不到什么报答!』
『可……可我过去给你的太……太少了!连着两年也没给你加过薪……』
陈向宇笑笑,眯起眼睛,真诚地道:
『没关系!我到您这儿做协理,原不是为了两个薪金!事到如今,我也不瞒您了,一切都直说了吧!到您这儿来,我是有我的想法的,我是想和您一起学着办矿,我是想在日后的某一天,搞一个自己的煤矿公司!』
他一怔,惊诧地道:
『你……你也想办矿!你?!』
『是的!想办矿!到大华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想过,以后,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经验办矿,我确乎不是为薪金,我是在探索一种经验!我用大华公司的矿业,用李公您的矿业,锻炼了我的办事能力。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呀!从这一点上说,公司给我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李公,我陈向宇由衷地感激您呢!』
他呆住了,他想不到面前这个天天碰面的年轻人竟这么野心勃勃!他被他的蓬勃精神感染了,一下子竟觉着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他仿佛不是在逃离一个动乱的旋涡,而是在启程奔向一个新的、更有诱惑力目的地,他生命的旅程还长得很呢!
他攥住陈向宇的手,恳切地说:
『好!好!干吧!向宇,好好干吧!到你真的能独立办矿的时候,我李某会帮你一把的!』
陈向宇摇摇头道:
『我感谢您,李公!可我有一个预感,我觉着大华公司是没有指望了……』
他心中一阵凄凉,是的,大华公司没有希望了,连面前这个和他朝夕相处的年轻人也认定它完蛋了!
他强作笑颜道:
『那么,向宇兄,看到大华公司办成这个样子,你真还敢办矿么?』他不自觉地在陈向宇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兄』字,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惊诧了。
陈向宇态度是坚决的:
『我要办的!一定要办的!煤炭是当今一切工业的基础,我们中国要想有自己强大的工业,非要拥有几十个、几百个强大的煤矿公司不可!否则,实业救国就是一句空话!李公,我总这样想,现在,该由我们来主宰自己工业的命运了!该由我们来安排中国工业的秩序了!我们中国土地上的煤矿,不能再一个个往外国人手里送了!』
陈向宇激动地摇着他的手说:
『李公,我钦佩您。尽管您失败了,我还是钦佩您!因为您远远走在许许多多中国实业家前面,最先将身家性命投身于煤矿事业,您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开拓出了一条血的道路!我相信,你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后人将记住你们,因为你们是有功于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语言像火,烤热了他那颗已经冻结了的心,他真感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竟这么理解他,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
『李公,还有一点,我也是佩服您的,那就是对待日本人山本太郎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您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而这种骨气,在我们的**官员、在相当一批中国实业家身上都是没有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在大华公司随您工作了这么多年!』
『可你也骗了我!』他想开一句玩笑,可话一出口,他就感到这并不好笑……
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向宇兄,你说到办矿,可你有办矿的资本么?!』
陈向宇道:
『有!我的父亲您也许认识,也许听说过……』
『谁?』
『陈汉奇。』
他大吃一惊:『陈汉奇?北方银团董事长陈汉老?你……你……向宇兄,你原是陈汉奇的公子?』
他恍然觉着是做了一场梦。六年,整整六年呵,这个北方银团董事长的儿子就在他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他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陈向宇刚到公司时,他训斥过他、责骂过他,他竟能不动声色地忍下来了,他竟那么服服帖帖地听他的喝使,这该需要何等的耐性呵!就冲着这一点,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比他强!
然而,他也恨面前这个骗人的年轻人!多少次,大华公司银根吃紧,面临危机,这个完全可以帮他忙的年轻人,却袖手旁观,不给他帮忙!他确凿地是在用他的资本、用他的矿业进行他的试验!这实在是不值得称道,这里面实在有一点阴险的意味。现在,他失败了,而陈向宇却胜利了,陈向宇从此可以轻轻松松地远走高飞了,从此可以着手干他自己的事业了……
他的手从陈向宇的手里抽了回来,脸孔上变了些颜色,不冷不热地道:
『向宇兄,你成功了,而我却失败了,这我承认。可有一点,请你记住,你是踩着我,踩在大华公司的肩头上起步的!』
陈向宇庄重地道:
『是的,我会永远记住这一点,记住大华公司,记住李公您!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还不想走……』
他冷冷插上来道:
『你还要把如何处理灾变的最后经验带走?』
『不!』陈向宇道,『我想在这最后的危亡关头能够助您一臂之力,借以报答您对我的多年栽培!李公,这,这确是我陈某的真心话!』
他默然了。
在这个问题上再谈下去也毫无意义,不管他相信不相信,不管他对这个年轻人如何评价,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他不愿在这最后分手的时候和他翻脸。
他将公司的事情最后向他交代了一下,终于还是友好地向他告辞了。在告辞的脚步迈开时,他固执地想:他还是要回来的,他一定要回来的!
他决不能让大华公司因此破产倒闭!
走上了大堤,他就开始揣摩:他将如何去应付那些**的委员老爷们;如何通过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们去打通**部门的各个关节;如何再度集资,以支付矿难赔偿和开拓新井。他想:就是田家铺煤矿完蛋了,煤田大火扑不灭了,他也要到邻近的青泉县去,到英国人的德罗克尔煤矿公司附近去再开办一个新矿!他要让实业界的同仁们看看,他李士诚干事业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决不仅仅只是在为后人们开路,而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开路!他还不老,他还不到五十岁,在人生的旅途上,在腥风血雨的人世间,他还能拳打脚踢地去开拓一个新世界!
野心勃勃的陈向宇的出现,像一道闪电,骤然间照亮了他面前黑暗的道路,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鼓起了他拼搏下去的勇气,他觉着,他衰败的生命中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不能就此倒下,他要干下去,他要以一个真正的实业家的勇气,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要回来的,他一定要回来的!他的四姨太还在这里,他的矿业还在这里,他的希望还在这里呵……
他的脸发热、发烫。他周身的热血在他那尚未硬化的畅通的血管中蓬蓬勃勃地循环、流淌着,他那颗强健有力的男人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着,他的博大的肺叶在尽情呼吸着这来自旷野、来自河床、来自成熟的麦子梢头的夜风。
活着,该有多好!
…………
他在大堤上走着,仿佛不是在仓皇逃跑,而是在悠闲散步。两个身着便衣的矿警,一个远远走在前面,一个悄悄跟在身后,他们好像素不相识似的。
走了有十几分钟光景,李士诚一行已悄悄通过了那段紧靠着西窑户铺的大堤。这十几分钟里倒也碰上了几个过路的乡民,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他神情自如,落落大方,当几个乡民走到对面时,他还主动给他们让路……
穿过了那段煤矸石铺就的护坡大堤之后,旷野里便有一条可以直接插往大路的田间小道,走在前面的矿警渐渐放慢脚步,在那小道的路口等他。李士诚赶上来,正要往坡下的小道走时,不料,迎面涌来了七八个田家铺的窑民。
他当时想躲,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转过身子,用背对着那些迎面走过来的窑民,想等他们过去之后,再往大堤下走。这些窑民刚刚从县城里为窑工们募捐回来,走在头里的三五个窑民骂骂咧咧地擦着他的后背过去了。当最后一个戴破草帽的中年人走过他身边时,无意中扭头看了他一眼,但他似乎一下子没认出他来。他当时好像有些惊奇、又有些疑惑,便重又扭头朝他看了一眼,然后三脚两步赶上了前面的人群,窃窃讲了几句什么;立刻,窑民们回转身,将他团团围住了:
『姓李的,你他妈的往哪儿跑?』
李士诚心里一惊,突然感到一阵极大的恐惧,他嘴里嘟哝了几句什么,便往大堤的一头退去。
『妈的,你以为你换了装,大爷就认不出你了么?!李士诚,就是扒了你的皮,大爷也认识你!走!跟我们到田家铺去!』那中年人将自己手里的一个沉甸甸的草包扔给身边的一个老人,上前就去抓他的衣领。
这时,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矿警赶了过来,猛地从怀里拔出短枪,用黑乌乌的枪口抵住了那个中年人:
『别动,动我就打你个狗日的!』
那中年人不敢动了,嘴里却在咕噜着:
『干什么?兄弟,这是干什么?!我……我们不过想和姓李的谈谈么……』
『放开他!放开!』
那中年人松开了手。
就在那中年人刚刚松开手的时候,又一个大汉一把搂住了持枪的矿警。那矿警当即开枪了,枪口在扭动中偏了一点,没有打中那中年人的脑门,却打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叫了一声,歪倒在大堤上,鲜血顿时从伤口处涌了出来。
开枪的矿警随即也被扭倒了,几个窑工扑上去压在他身上,没头没脸地打他,踢他,用脚踩他的脸、头部,用砂礓石砸他的腿。他没命地嚎叫起来。
这一切,把前边路口上的那个矿警吓坏了,他根本没敢往前凑,便顺着小路,一溜烟地跑掉了……
李士诚就这样落入了田家铺窑民手里。
简直像开玩笑一样。
他的手被他们用两条裤带捆了起来,捆得很死。他们捆他时,他还挣扎,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屈辱,他觉着这很不合理。他是什么人?他是大华煤矿公司总经理,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他!……
他喊了起来:
『住手!你们住手!我李士诚不会跑的!我要见你们田二老爷,我有话要和他说!』
那受了伤的中年人劈面给了他一巴掌,打得他鼻孔里冒出了血:
『狗日的!现在想到俺二老爷了!你他妈的早干什么去了?』
鼻孔里的血像泉水一样流个不息,流到了他嘴里,流到了他的脖子上,他害怕了,他从未经过这样的事情,他怕自己浑身的热血会顺着鼻孔全流出来,这样,他就会死的。他试图用手去堵住流血的鼻孔,可手已被捆住了,无奈,他只好去求他们:
『放了我,放了我吧,我……我……我的鼻子在流血……』
回答他的又是一个耳光:
『死不了你!你这才淌多少血?我们一千多兄弟爷们死在窑下要有多少血?!走!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他被他们拖走了。他没想到太大的危险,他断定面前这帮杆匪一般的窑民是不会对他下毒手的,他们没有胆量——不但他们,就是他们的田二老爷也没有胆量杀死他!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大华公司总经理,还是个有脸面的人物!
他只想赶快见到田东阳田二老爷。他和这帮窑民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他和他们不对等,没法对话;而和田二老爷却是对等的,是有可能对话的。
他变得强硬起来,他不能在这帮无知的窑民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怯懦、表现出自己的无能,他要用自己应有的威严震慑住他们。
走在大堤上,他冷冷地对他们说:
『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你们会后悔的,你们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大华公司垮不了,你们还要在公司做工,我劝你们好好想想!』
那帮人根本不睬他。他们已派出两个人跑到镇上报信,其余的人警觉地守在他身旁,不住地拳打脚踢,逼迫他快走。他们也害怕突然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这时,他又有了一丝侥幸的心理。他想,也许那个溜掉的矿警会赶回去报信的,只要他能及时地赶回去,将情况告诉陈向宇,陈向宇决不会见死不救的,他一定有办法促使镇守使张贵新带兵前来救他。
他要尽可能地将面前这段道路延长。
他不管那帮窑民听不听,仍自顾自地讲:
『工友们,你们何必要搞到这一步呢?你们何必要把什么路都走绝呢?为人处世总得想着要为别人留一条出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你们……你们就没想到过这一点么?』
那帮人还是不理。
通往田家铺西窑户铺的道路,在他们的脚下一点点缩短,渐渐地,李士诚看到了西窑户铺的一片灯火,看到了大堤下的一片片时隐时现的人头,听到了从西窑户铺方向的夜空中传来的阵阵呼喊和喧嚣。
显然,两个前往田家区田二老爷府上报信的人走漏了风声,在田二老爷闻知这个消息之前,镇上的窑民们已得知了消息,他们全从自己的破草庵、破茅屋、破土房里钻了出来,涌到了街面上,涌到了连接着大堤的道路上。好些人举着火把,那火把上呼呼燃烧的火焰隐隐约约照亮了他们愤怒的面孔。
他听到了他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喊:
『揍!揍死这个**操的!』
『让姓李的王八蛋给我们兄弟爷们抵命!』
『背石沉河,把李士诚背石沉河!』
『揍呀,爷们,都去揍呀!』
…………
他突然紧张起来,突然感到了生命的危机,一种真正从心里冒将出来的、混杂在他周身血液里的极度恐惧,使他整个身体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在这帮被愤怒和疯狂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窑民们面前,他是什么也说不清的;即使能说清楚,他们也不会听的!他们认定害死了那一千多名窑工的,是他,而不是别人!他们要报仇,他们要索还血债,他们要为他们死去的父老兄弟伸冤!
这时,他多么希望在这帮愚昧而可憎的窑民们中间看到田二老爷呀!尽管这个田二老爷也是他的对头,尽管这个田二老爷也蛮不讲理,可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只有田二老爷能够救他!因为,他们毕竟都属于这块土地上的上层社会,上层社会的规范、秩序、法则,将毋容置疑地保护他的生命,他懂得这一切,田二老爷也懂得这一切;而这帮愚昧的窑民们不懂,他们只服从于自己执拗的感情,在这种执拗感情的驱使下,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他不走了。
他站在大堤上,一步也不愿走了。
他近乎绝望地喊:
『我……我要见田东阳先生,我要见你们的二老爷……』
『滚你娘的吧!』身后,一个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一脚将他踢下了大堤。
他跌跌撞撞从大堤上栽下来,还没站稳脚跟,堤下一帮窑民们便涌了过来,他的眼前黑压压地倒过来一片人群,倒过来一座森严的山……
他倒在嵌着砂礓的土地上,他被捆住的胳膊压在他自己笨重的身体下面,干燥的砂礓将他的胳膊和手掌硌得很痛。他感到自己像一只可怜的蚂蚁,被骤然扑将过来的喧嚣淹没了,他的眼前闪现出翻滚的星空,翻滚的火把,翻滚的人头。他惊叫着闭上了眼睛。这时,他的头部,他的上身,他的腿,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遭到了袭击。拳头、脚尖、棍棒像旋风一般在他身边呼啸着,几乎完全吞噬了他的呼救声。
大堤上的那帮人跑了下来,他们试图阻止住疯狂的窑民,他恍惚听到他们在喊:
『都住手!住手!让二老爷发落他……』
后面的话他听不见了……
这时,他的神智还是清醒的,但他已没有力气叫喊了。他蜷曲在地上,像一条可怜的狗一样,听凭那些疯狂的人们在他身上发泄自己的仇恨。完了,一切都完了,由于生命道路上的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他竟被这些迟早要被别人送上肉案子的人们先送上了肉案子!
偌大的世界原来是个令人恐怖的大肉案子呀!
这是一个发现。然而,他发现得太晚了,他陷得太深了,他拔不出自己的脚了!他想,也许他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办矿,也许他应该在第十二次失败之后,悠悠荡荡地混过他的一生,他会混得很不错——至少不会这么不合情理地死在这帮暴怒的窑民手里!
他在这临死的最后一瞬,在含着血泪的痛苦**中又想起了陈向宇,想起了他那野心勃勃的话语:『我们中国要有自己强大的工业,非要拥有几十个、几百个强大的煤矿公司不可!』不容易呀,真不容易呀!仅仅两个小时以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观念,他深深感到,陈向宇是太幼稚!太爱空想了!这块土地,这块苦难的土地上是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几十个强大的煤矿公司的!在这块古老而广阔的土地面前,中国实业家太年轻、太渺小了!
自然,他希望他比他强,希望他能成功,希望他能将脚下这块土地彻底征服,但是,希望毕竟是希望呵……
思路在这里中断了,这时,他血泪蒙眬的眼中看到了星星,看到了星空下一个悬在他身体前上方的、尖尖发亮的三齿抓钩,他知道,那抓钩是乡民们刨地用的。那抓钩落了下来,第一次没打中他,握抓钩的人身体向前倾了一下,又将抓钩举了起来。他听到了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一句充满仇恨的话:
『狗娘养的,我要你为我死在窑下的三个儿子偿命!』
抓钩又一次落了下来,他惨叫起来,他在血泊中挣扎起来,他的灵魂在死亡造成的极度痛苦中飘离了他的身躯……
田二老爷闻讯赶来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墨蓝色的星空下,依傍着古黄河大堤的土地上,静静地站立着一大片衣衫褴褛的人们,这些人木然地看着田二老爷,似乎想听听他们的二老爷要讲些什么。
二老爷什么也没有讲。
二老爷呆呆地伫立着。在两只火把的照耀下,他仿佛是一尊古铜色的神像。
二老爷昏花的老眼里又一次滚出了浑浊的泪珠,泪珠很响地落在脚下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