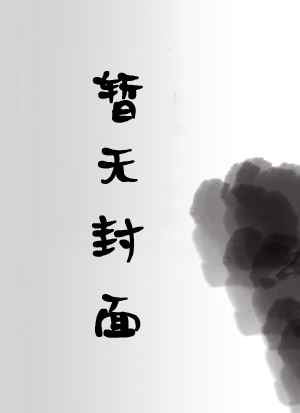宋晚辞降下车窗然后目光停在一家普通的花店上,安静几秒,她应声:“嗯。”
薄景年抬眸顺着宋晚辞的视线看过去,目光顿了下,平静收回。
宋晚辞准备推开车门,还未下车时身后传来薄景年低低的嗓音,“你是忘了你花粉过敏?”
宋晚辞停下动作,转过脸看向他,“我知道的。”
“我只是想买一束木棉花带过去而已。”
她眉眼温静地说完,然后打开了车门。
她母亲是最喜欢木棉的,自住进温园后她就没有去过墓地。即使是花粉过敏,她也仍想带一束木棉过去。
仅此而已。
外面的雨愈下愈大,她将要下车时,手腕被人捏住。
宋晚辞回眸,目光平静,她并没有开口说话。
沉默对峙。
“我去买。”薄景年淡淡开口。
他说完松开宋晚辞的手腕,然后靠近她,伸出手臂替宋晚辞关上了车门。
五分钟后,花店门口,身形欣长的男人撑着一把黑色的伞走出。
花店玻璃门被关上时,门上的彩色铃铛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
薄景年左手拿着一束白色的木棉,神色淡淡地看向降下的车窗。
车门被打开,薄景年坐进去,面色平静地看向宋晚辞。
他并不开口,手中的花束也没有要给宋晚辞的意思。
他一惯的冷淡,看向他人时面无表情,辩不出喜怒。
但宋晚辞却知道,这是他情绪不好时的表现,三年时间她没看懂过眼前这个男人,但脾性总是能摸清楚一些的。
两个小时的车程,车内的气氛太过于安静,宋晚辞并未主动开口打破沉默,她只是目光淡淡地看向车外。
到墓园时,宋晚辞垂下眸子,出声道:“薄先生能把花给我吗?”
薄景年目光扫过她,眸色沉沉。
最后那束花还是到了宋晚辞手上。
雨已经停了下来,路面上仍是cháo湿的。宋晚辞下车,鞋跟踩在青石台的路面上。
她踏上一层层的台阶,手里抱着的是那一束白色木棉,落尾的裙摆似乎也沾染上了台阶的湿意。
穿过一条条石径小路,最终到达一坐墓碑前。
宋晚辞站立于墓碑前,淡淡垂眸,目光停在墓碑上的刻字,最后回到那张黑白的小像上。
她弯腰,抬手抚过相片上的雨点,然后将手里的木棉花靠于墓碑放下。
宋晚辞原先就是个安静的性子,在这一点上她和她母亲是相似的。在她母亲去世后,宋晚辞完完全全的将自己封闭了起来。
那时她是九岁,从不爱笑,每日在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只是抱着那个小熊玩偶。
后来她病的彻底,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
持续了近半个月的感冒发烧,落下身体虚弱的毛病,偏又不肯去医院,日复一日的这样拖着,身体也调养不好。
住进温园后,一直每日汤药调理,身体上的问题是逐渐变好,但心理上的问题却愈发的严重。
这一点宋晚辞很清楚,她从原先只是睡眠不好,到现如今的深夜不断惊醒。
似乎再无转好的可能。
指尖触到墓碑,带着雨水的湿润与冰凉,一如她幼时那日触碰到母亲的身体时一样。
宋晚辞收回手,原本绾起的乌发沾染上了空气中的cháo湿,聚集着变成一滴水珠,从宋晚辞的侧脸处缓缓滴落。
雨天总是要冷一些的,可宋晚辞因为木棉花的缘故,脸上以及露出的皮肤都起了一层浅浅的粉色。
再一次的花粉过敏。
雨点再次落下的时候,宋晚辞的头顶出现了一把黑色的伞,替她遮挡住了所有的风雨。
薄景年立于宋晚辞的身侧,右手撑着伞,目光极淡地扫过面前的墓碑。
他并没有开口,只是沉默的陪伴。
男人的身形要比宋晚辞高出许多,从远处看过去,更衬得宋晚辞身体消瘦。
宋晚辞一身黑色的连衣裙,裙摆落在小腿处,白色的花边是唯一与之不同的颜色。
两个人的身影站在一起时像是水墨丹青画,
……
宋晚辞回去后的当晚就发起了高烧。
她缓慢的吞服下药丸,任由苦味在口腔内蔓延开来。
吞下药后,她放下手里的玻璃杯,淡淡出声:“薄先生不去休息吗。”
昏暗灯光下,男人坐于沙发上垂着眉眼,听到宋晚辞的声音后他才抬眸看过去。
眸色沉了下去,一如外面黑暗的夜色。
薄景年还是平常的神色,可眸子却冷,他低哑开口:“宋晚辞。”
“再这样病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住院。”
是一句平常的陈述句,语气却也冷。
宋晚辞安静听完,她走到薄景年身侧,微微弯腰,目光直直地看过去问:“薄先生是在关心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