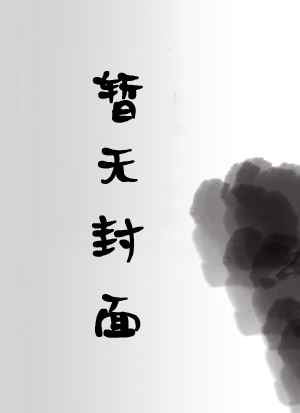眼看着那方小木盒子,我愣在原地,想喊,想不出声,想动,却动不了,目光和思维完完全全被眼前景物禁锢。
一旁的孟晓溪已经再次哭出声来,将头埋在了我的怀里。
不说她不敢看,连我,也是觉得心惊胆战。
因为,那木盒子里头居然放着一个男婴的尸体,全身泛紫,两眼微闭,肚皮上还连着一小截未完全清理的脐带,全身湿漉漉的。
这不像是埋进去了很久的婴儿,反倒让我感觉是刚刚才进到坟墓里头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在我离家这么多年的时间里,爹娘又生了一个弟弟,而且还非常不幸的夭折了。
只是,爹娘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这一念头才刚浮现,我便心中一阵潸然,因为,我这才想起,我的爹娘也躺在了这旁边。
这也就是说,至少从现在开始,我和我爹娘,还有才见一面的弟弟已经完完全全的阴阳两隔了。
只是,在悲痛之余,我却又有些不太确定,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爹娘不可能在再生了一个之后不告诉我啊?
我纠结到了极点,悲伤和困惑交织心头,将棺材盖缓缓的拿了起来,就要将它给重新盖上。
眼看着盒盖缓缓合拢,我轻叹口气,不忍再看,想要将目光别到一边。
只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婴儿的那只小脚印入了我的眼帘,让我全身一颤的同时不得不再次将盒盖一掀,将整个婴儿再次露了出来。
那只小脚平放在那里,脚底板正朝着我,上面,竟然有一块黑色的印记,而这,也正是我再次一惊的原因。
因为,在我的左脚底板上面,也有一个黑色的印记。
我二话不说,立马脱了鞋袜,弓着身子朝自己脚底板看了过去,却见同样一个印记出现在我的脚心,看形状,几乎一模一样。
这让我惊骇莫名,如果说这木盒子里躺的是我弟弟的话,那也不可能在同一位置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胎记吧?
我记得王长生对我说过,这印记是我一脚踏进了鬼门关后留下的,难道说,我这个已经夭折了的弟弟也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此时的我,看着这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好像自己掉进了某个不知名的漩涡之中一般,根本理不出半点头绪,也根本找不到半点方向,这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好似一团迷雾一般笼罩着我,让我心急如焚的同时却又苦苦不得解脱。
孟晓溪以为我是伤心了,凑过来低声安慰我说:“陈寿宁,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别太伤心了。”
但是,孟晓溪不说还好,一说我更是大吃了一惊,一下子猛的站了起来,着实吓了她一跳。
我想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于是我踏前两步,一把捡起那之前被我拔了的小树,瞪着两眼细细看起小树身上的字来。
这笔迹我还是非常熟悉的,是我爹所留,虽然模糊,但“陈寿宁”三个字却骇然在目,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一点,那就是如果眼前这个躺在盒子里的婴儿如果真是我弟弟的话,怎么可能和我同名,爹娘也完全不可能做出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来。
但是,一想到这我更是心惊不已,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意味着……棺材里头躺的就是我?
突然之间我有些想笑,这未免也太滑稽了些,我这不好好的活着并且长到了十八岁么,怎么可能会好端端的埋在这棺材里头呢?而且,这分明还只是个不足月的婴儿。
我感觉自己要疯了,抱着脑袋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将头深深的埋在了坟土堆里,感觉自己好像在做一个真实得有些可怕的噩梦一般。
孟晓溪一直战战兢兢的守候在我旁边,眼泪唰唰的流,可能是被我吓着了,我才一抬头她便像只受了惊吓的小兔一般看着我,不自觉的后退了几步。
看她这样,我才想起自己刚才是否太失态了些,于是挤出一丝笑意对她说:“我没事,只是一时之间接受不了眼前事实而已。”
孟晓溪点了点头,依然有些胆怯的走了过来,低声说:“我们……还是把这小棺材先盖起来吧。”
我知道她怕,于是点了点头,再次拿起那木板想要盖上去,只是,我这才将木板一翻,便又听得孟晓溪一声惊呼传来:“陈寿宁,你看,是张相片!”
“相片?”我听后一愣,将木板反转过来一看,这才发现,原来在这小棺材盖上竟然还贴了张照片。
黑白色,单单只是一个头部像,看上去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看了让我一阵心慌。
只是,心慌的同时我又有些疑惑,一张成年人的照片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婴儿的棺材盖上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遗像上的这人无轮是从眉目还是脸型,都与我相似到了极点,说得直白一些,竟然就像是三十多岁的我一样。
我又凑近了些,想看出一些端倪,只是这一看,还真发现了问题,在那照片下方,竟然还写了一行字:纪念陈寿宁三十六岁生辰!
我倒吸了口凉气,一把将这棺材盖给扔了,感觉全身冷得出奇,不自觉的打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