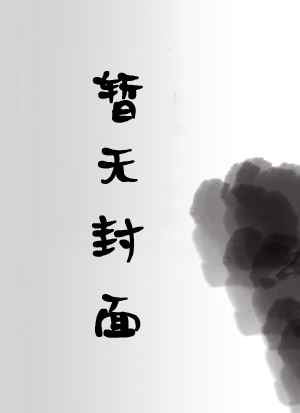我跌坐在地上,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此时的心情。
这并不完全是感观上的刺激,最主要的是,眼前的情形切合了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场景,更是撩动了我脑海深处那根最为脆弱的神经,让我一时之间完完全全的懵逼了。
透过大开的门看去,那低矮房屋的房梁上,悠悠吊着两个身形佝偻的老人,其中一个是我从未见过的老头,而另一个,则是那刚刚还坐在门前搓麻绳的老太太。
只见两人舌头伸得老长,两根崭新的麻绳将两人脖子拉得长了几分,肌肉扭曲的脸上两眼因为痛苦而充了血的眼睛瞪睁,既像不甘,又好似带着安慰,正低低的俯视着一旁门板上放着的两个幼小的身体。
一家四口,两小孩淹死,两位老人上吊,不正是奶奶曾经跟我说的那个事么?
我倒吸一口凉气,几乎连滚带爬的朝着村口跑去,才跑出两步才想起依然呆若木鸡的孟晓溪,只好又转身一把拉住她的手,不管不顾的朝着村口冲了过去。
好在的是,孟晓溪这一声尖叫并没惊动村里人,我一面狂奔,一面回头观望,见无人跟来,于是又跑了好大一截距离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依然像失了魂一样的孟晓溪,一连喊了她好几声都没回音,恍恍惚惚的样子过了好半天后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把扑到我的怀里哽哽咽咽的哭了起来。
感受着怀中全身瑟瑟发抖的娇躯,我心中泛不起半点涟漪,脑海之中满是疑惑,刚才那一幕依然尤在眼前。
我想了想,3d6db1ce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村口第一家发生的事如果用巧合来说的话,那未免也太没有说服力了。
但如果不是巧合,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已经淹死或者上吊的人,是不可能再死一次的。
还有就是,为什么那帮人要将孟晓溪浸猪笼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同样是有着好合泉的牛背东村,为什么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呢?甚至连房子都完全变了。
我满头雾水,拼命的揉着自己的脑门,似乎想从里头挤出一个答案似的。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
“啪嗒,啪嗒”。
是脚步声,现在的我好像惊弓之鸟一般紧张到了极点,放眼望去,因为天还没亮的缘故,我看得不甚清晰,但隐约间可以确定,有一个人正缓缓的朝我们这边走来。
我推了推低声哽咽的孟晓溪,意示她站起来,情形一有不对就赶忙跑。
孟晓溪也是两眼一瞪,同时回头看去,眼见那薄雾之中的人影越来越清晰,到了最后已然能完全看清,定睛一看,顿时喜上眉梢,差点没欢呼出来。
这人,竟然是秋娥婶。
我捏着孟晓溪的手,就要走过去问她怎么回事,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却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
只见秋娥婶面色木然,像没看到我一样,耷拉着眼皮,像没睡醒似的,一步一挪的迈着步子,身体僵硬得像个机械人一样。
而与此同时,我这才看清,在她身后,竟然还有一个人,紧跟着她的脚步,也是一步一挪,步调非常的一致。
但是,也正因为这极为一致的步调才让我头皮发麻,拉着孟晓溪悄然的躲到了一旁的树后,探出脑袋想看个究竟。
只是,等我真正看清秋娥婶身后这人脸的时候,顿时本能的捂住了自己的一嘴,一颗心差点没直接从喉咙里跳了出来。
这人,竟然是林子叔!
只见他一身黑衣,整整齐齐的,不染一尘的布鞋甚至连底子都是白的,胸口绣了个金丝大字,细细看去,是个老写的“寿”字!
这种衣服,只有一种人能装,那就是死人。
林子叔身上,竟然穿的寿衣。
我脑海一阵眩晕,就算是白痴也想得明白,此时的林子叔,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出现在我眼前。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仅剩的结果就呼之欲出了。
我不自觉的打了个摆子,看着他两悠悠的走远,之后才拉着一脸懵懂的孟晓溪悠悠的跟了上去。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突然间想知道,这整个村子里唯一熟识的两个人倒底要去干嘛?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才跟了两人一路,一个眨眼,这两人竟然不见了,就像是凭空消散在了雾中一样。
我一愣神,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环顾四周看了一圈,这才发现,原来不觉之间,我竟然已经来到了村里的坟地。
只见四周墓碑林立,或大或小,参差不齐的座落在那里,我倒是没觉得什么,只是有些疑惑秋娥婶两人怎么就不见了呢,但是,孟晓溪不同了,她是城里的孩子,很少见到这种场面,捂着嘴全身不住颤抖,像只鹌鹑似的揪着我的衣角,低声问我:“寿宁,这是你家的坟地么?”
她这一问顿时点醒了我,让我霎时间眼前一亮,想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村里活人我没一个认识的,但是死人是变不了的,我没道理不知道啊!
相对来说,这坟地与我记忆之中有很大不同,虽然也是一个挨一个的,但是,比起记忆中来却更是密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