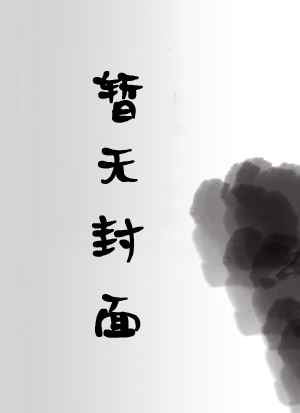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叽叽,喳喳,叽叽,咕咕……”
江南春的楼下传来了一群小鸟儿的鸣叫声。她拉开窗帘,将窗户使劲一推,天空中的鱼肚白便映入眼帘。天是朦胧的,看似悠远而迷茫。目光所及的地方能影影绰绰地看见小树在雾霭中若隐若现,手一伸似将一缕轻纱抓在了手里,往回一缩又空空如也。饿了一晚的小鸟儿,似乎在这迷雾中穿行惯了,或许它们有一双精灵般的眼睛能够穿透这片迷雾,看见背后的阳光。于是早早地呼朋唤友,奏响晨曲。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江南春对此深信不疑,她等不及太阳从东边那看不见的地平线上升起,便骑着三轮车伴随着“丁零零——丁零零——”的清脆铃声出发了。随着车轮的转动,她开始运动自己的肢体。当太阳渐渐升起,露出了她的半边红脸时,江南春已与自己的伙伴——那辆破旧的三轮车来到了朝阳门。看见清晨里一张张或年轻或年老的面孔,他们背着形形色色的包,行走在马路上,便看见了希望。
“油条,五毛嘞——”
“刚炸的,又香、又脆、又大的油条嘞——”
一个面如敷粉的女娃大声地当街叫卖着。
三轮车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火膛里映出了红光,炉子上架着的油锅不停地翻滚,姑娘将一根根细长的白面块轻轻放进去。不一会儿,细细长长的白面块儿开始膨胀了,慢慢地有了淡淡浅浅的黄,那黄越来越深,过了一会儿,油锅里出现了一根根金黄酥脆的油条。
“我来两根油条,多少钱?”
“一块。”
“你这儿比人家的贵,他们才卖三毛哩。”
“我这儿油好,油条个儿也大。不信我白送你一根尝尝,你再花三毛钱买一根别人家的吃在嘴里比比。若好,您再回来。”江南春不肯让步。从小父母耳提面命的话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她相信那些有过比较的客人,一定会回来。所以她一直面带笑容据理力争。
“嘿,这女孩儿够绝,一点儿也不肯让步。”讨价还价的人“咔嚓”咬一口油条,便咧着嘴乐了。
江南春却来不及看一眼和她说话的男人。只听顾客中有人喊:“城管来了!城管来了!”江南春一惊,吓得捏着面条块儿的手一下子伸进了油锅。“妈呀!”江南春惨叫一声,那个刚才叫喊“城管来了”的男人一把抓过她的手,“别动!你赶紧跑到胡同背后去等着,我帮你把车推过去。”
江南春仍然没有看仔细这个男人的模样。当务之急,也只能让这位自告奋勇的男人将车推走。
“谢谢。”
“来,你把手放进盐水里浸一浸就没事了。”
“城管走了吗?”江南春像只惊弓之鸟,左右张望。
“走了,我已替你看过了。”男人道。
“哦。”听说安全了,江南春这才痛苦地皱着眉头、龇着牙,像害了牙疼一面“咝——咝——”地往外哈着热气,一面听话地把手伸进凉凉的盐水盆里。“咝——”江南春又哈了一口长气,她感觉舒服了一些,刚才火熛熛的疼没有了。
“谢谢您啊!今天要不是碰上您,我那小摊儿肯定就让他们给收走了。”虽然江南春为小三轮车的幸免于难而高兴,但今后的那几天不能正常营业,预算中的银子也泡汤了。一想到每天的吃穿住行没了着落,她心里就没法儿不惆怅:
“唉!倒霉呀。钱没挣着,还把手烫了。”
“嗯,那是。你这手伤了,至少得养一个星期。”男人笃定地就事论事。
江南春手上的疼痛消退了些,才有工夫仔细打量眼前的男人。要是世间所有的男子都像那电影里的白马王子该多好呀——高大英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江南春记得自己在十六七岁的时候看过《上海滩》,那片中的许文强玉树临风的模样,她就觉得他简直帅呆了。她还暗暗在心里给未来的丈夫刻了一个许文强似的模子。只是可惜,这个男人不是许文强,自己也不是冯程程。自己和这个男人素不相识,他为什么帮自己?
江南春使劲猜度着眼前这个男人的年纪:三十?哦!不,看起来更像四十。噢!或许还不止。难道有五十?切,不会那么老吧!?她猜得头痛,便甩了甩头,自己都嫌自己庸俗。
对一位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男人,却要大费周折地去猜测,也太可笑了。何况,他那么平凡。就犹如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微尘,一棵参天大树中的一片树叶儿。然而他给江南春的感觉又是奇妙的,他不起眼,却并非没有分量。他是善意的、宽厚的。就犹如他那人——朴实得像墙边院后的一棵老榆树,普普通通得可以让人忘了他的存在。
“早,又出摊啦。”过了一个星期,老张又看见了那个把手烫伤的小姑娘,跑完步往家走时和这个姑娘打招呼。
老张笑得像个弥勒佛。江南春想不出来,这个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人,为何如此快乐。
“嗯。张大哥,锻炼完了?今天还来两根油条?”江南春也咧嘴笑着。她的笑是发自内心的,是他乡遇故知的愉快。自从手伤之后,她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张春生,可她还从未叫过他的大名。
“没错,来两根。”老张从口袋里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