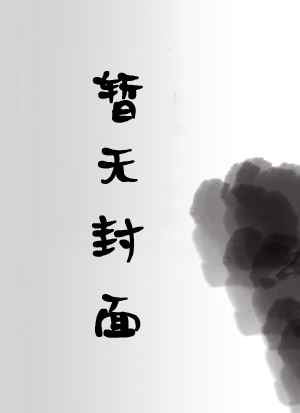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第二天七点半了,我才慌忙起床。心想,这是怎么说,医生一会进来非笑话不可!我看见黄大姐已经在收拾床铺,用那种一根筋热水工具,烧着开水。我赶快去病房斜对门的水房洗脸。回房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堆人,有人高一声低一声地说话。我以为医生找我这个陪护,忙挤上前去,却见黄大姐伸着一只手,食指直冲那个小护士上下乱晃,嘴里叫道:“我日麻就望你看我不顺眼,莫道我们乡下人好欺负,我日麻从小不受哪个的话,叫你个小娃子来教训我,你找错了人!你也不看看,那是不是我的床铺,你日麻硬是觉得我好欺负耶啥子!”我一看,那分明是我的床,还没有来得及叠被子,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老天啊,还叫黄大姐代我受过--一定是那个小护士指责她了。
好歹咱是男子汉大丈夫,自个的事,决不叫别人扛着,忙走到小护士面前,打拱作揖,哼哼哈哈道:“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是误会了。这都怪我,起来迟了,不怪黄大姐,不怪黄大姐。我有罪,我有罪。”黄大姐一看我出来说话,便不言语了。小护士狠狠朝我剜了一眼,嘴张了张,没有说出话来。我又点头哈腰(是不是很丑?错了,那种状况下,我特有经验,非如此不足以平民愤“嘿嘿嘿,看把您气得。真是对不起,对不起。您如果有气,就骂我吧。这都怪我,都怪我。”又拧过身,说:“黄大姐,是我闹出的一场误会,大家都把气消了吧。”我看见小护士眼角一弯,快要笑出来的样子,但是却抿了回去。我见有泪光一闪,借着李护士的解劝,顺势走了。
我很快知道,小护士的名字叫阿梅。听起来一点也不象个女孩子的名字。据黄大姐说,阿梅年龄不小,27岁了,丈夫在省内某个市工作,最近两口子正“闹仗”呢。“活该,这个挨刀子的花花儿。”黄大姐用这么一句刻毒的话结束了她的介绍。“难怪她总是沉着个脸。”我说。“大姐,她心情不好,您人大量大,也别太怪她。”
过了一会儿,有个小护士进来说:“42床,王护士叫你到一楼帮忙拿东西。”那是一种命令的口气。我慌忙应声,让人家受了一堆委屈,这是给了一个赎罪的机会呀!再说,在这里,我可不想去得罪一个护士!拿东西嘛,我有的是力气!不怕的。邻床的小陈也一骨碌爬起来,跟我朝楼下走。进了一楼仓库,只见阿梅坐在一张凳子上,朝我瞪着双眼。那可是一双美目,我身后的光线在她双眸上一闪,很有几分韵味。我心里故意找些文学词汇来美化她。负罪之心嘛,原也情有可原。我呵呵一笑,问她:拿什么呀?您吩咐吧。小的今儿就是你的手下,任你使唤了。她低下眼睑,正要张嘴说话,小陈进来了,便打住,说:小陈,把那几床被套拿上去吧。小陈答应,我也朝被套走过去,她却在后边说:小三(你一会儿拿这边的。我心里噔地一响,她的话音里,似乎别有一种哀楚,一种我说不出的感觉。我不由得站住,看着小陈拿着被套出去了。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前半间被隔出来做了门诊,后一半就成了库房。我看着小陈抱了一大抱被盖出去,竟觉得不知怎么说话。毕竟,我跟阿梅没有任何交往。这几天在医院,我的随和,大方,能干(所在的地方,一般都有一堆人围着。我说过,我喜欢开玩笑,我想,说笑话,也许正是我游戏人生的一种方式。但这其实跟我一向正板的个性,是不相符的。
“你不是有那么多笑话吗?怎么不言语啦?”阿梅终于说话了。我不知道她怎么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她不是叫我来干活吗?这,叫什么活?我奇怪地看着她。显然,我心里有几分恼火,一个小女子,即使长得象天仙,也不应该这么居高临下地对我说话。而且我发现,她没有穿戴护士的行头。上身着一件紫色的薄毛衣,勾出胸腰部清晰的轮廓,下身穿一条我说不上颜色的牛仔裤,绷出滚圆的臀部和大腿。我心里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性感吧。
“你叫我来干活,还是来说话?是不是想公报仇哇?”我双眼直视着她,我的目光,向来不怕光彩照人的女人。何况,我又不是二十岁的毛孩子!什么样的阵仗,我也多少见过些。她大概受不了我的语气和眼神,将视线移到我的胸前,竟有些怯怯的样子了:“你,总是这么厉害吗?你不知道,查房的时候,你叫我多么难堪!”我想,是啊,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被一个乡下人抢白,那多没有面子啊!哎,她那可怜的自尊心,一个贫弱的城里人的自尊心,活活被我给毁掉了。我有几分幸灾乐祸,但是,大家已经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可恶的坏人。我心软,尤其面对一个楚楚可怜的女子,我不忍表现得太过分。我说:“再向你道歉行吗?我可没有任何动机叫你难堪。唉,都是我不好,睡了个懒觉,惹下一串串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