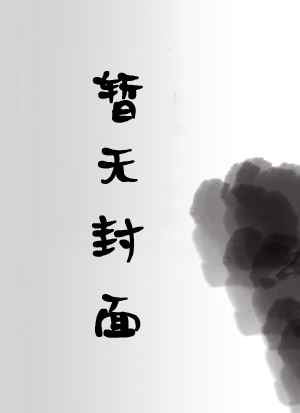有些欣慰,同时感到忧愁。
现在这孩子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又开始别扭起来。
啧,难搞。
……而且上一次就是她先找他说话,这次怎么也得他来吧。
他可是男孩子欸!
她这么想着。
于是就没有再去主动说话。
又这么过了一星期。
那少年却表现得越来越放肆。
他频频迟到早退,甚至最后不来上课,一度不见人影。
偶尔回来,趴在桌上,倒头就睡。
他到底是出去gān什么了?
友枝心里的好奇感愈发加重,对他又有些不顾前途的行为感到生气。
趁着那个人回学校取东西,友枝偷偷跟在他身后,保持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
没想到,她最后跟着祁凛去了镇子边的稻田。
祁凛提着书包,走在前面,大风把他身上白色的校服衣摆chuī得猎猎而动,火金色的夕阳,几乎与金huáng的稻田连成了一片。
友枝跟着,一边新奇地打量着四周的景色。
她之前也来过这里,但是那也是好久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已经快要入冬,水稻田里是金huáng一片,稻草蓬松而gān枯,带着隐约残存的米香味,不远处是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微风拂过,清跃萧森。
水稻田的泥道边上,有条huáng狗忽然汪汪叫着跑来,摇着尾巴,跟在少年身后。
他低下身子,摸了摸它的头,继续往前走。
友枝看了一会,然后跟了上去。
跟着他走过稻田,来到宽阔的河边,她站在树影之后,而少年坐在岸堤的台阶上,眺望着河面。
这么待了一会。
忽然祁凛拿起一块石头扔出去,接连dàng出十几个水漂。
大huáng狗摇着尾巴过来,坐在少年的身侧。
一人一狗就这么坐在岸堤上,意外和谐。
友枝忍不住勾唇,随后极目眺望,看到水面上有一条破渔船,船上的老翁撑着木船桨,慢慢悠悠地从水面上划过。
老翁唱着一首悠长的歌。
“水迢迢嘞——冯虚御风——”
她又看向了祁凛。
他似乎很疲惫也很厌倦,闭上眼睛,微仰着下巴,把手撑在两侧。
河风把少年漆黑的碎发chuī动,白色的衣摆向后。
也chuī起她鬓角的长发。
友枝扶着树gān,粗糙的触感滑过指腹,她却兀自看着不远处的祁凛。
见他白皙的肤色染上金色的霞光,就那么静静地待了好久好久,一动不动。
她见状,眼睫轻动几下。
总觉得……他好像很孤独的样子。
像是承载了很多,像是陷在泥土里的花朵。
忍不住很想……靠近。
她轻轻环顾四周。
这里确实能够很好地放松心情。
……所以让他忧愁的事情,是不是很多?
那条huáng狗好像看到了她,突然叫起来。
少年应声回头。
她下意识地躲到了树的后面。
手按着树gān,而心脏却在忍不住发跳。
友枝低下头,看着稍显泥泞的鞋尖。
————
体育课下课早。
大家还没回来,一整个走廊里都静静的。
友枝走上楼梯时,发现那个少年靠坐在窗边,指节夹着一根烟,稀薄的烟雾缭绕,又在窗外的风中消散。
她想了想,走到他面前,看着他。
祁凛懒懒回身,抬起眸,看到了友枝。
他的目光淡淡的,没有说话,随后又把头转了回去。
“你还要像这样多久?”她终于忍不住发问。
“不上课,不写作业,还总和老师对着gān。”
“你最近真挺飘。”
“关你什么事。”他声嗓冷淡,也不看她。
“祁凛,发生什么事了?”她上前一步问,攥住他的手,想要阻止他吸烟的动作。
他眉头一蹙想挣开,而友枝按的紧,没挣开。
祁凛声音冷淡:“把手拿开。”
“我真的搞不懂你到底在闹什么脾气啊?”她真的有点不理解,“你就跟那陈年老醋似的,臭石头脾气,也不会哄女孩子,你再这样我就真的不理你了。”
他掀起眼帘看她,忽然问了这么一句:
“友枝,你把我当什么?“
女孩明显一愣。
“你……”
“同学,朋友?需要被关心的不良少年?还是一条可怜虫?”祁凛说着,看着少女那张面容姣好的脸庞,被窗外的夕阳映照的有些发红。
她看着他,不语。
“我之前就问过你。”他声音淡淡,把烟条拈灭,心中的意念近乎执拗:“今天再问一遍。”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