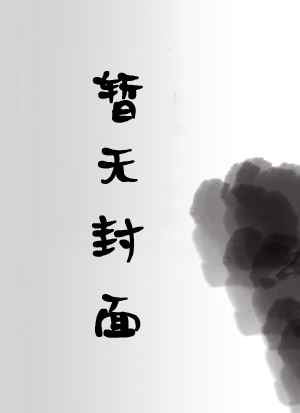下午她开完会,打车去了市中心的蛋糕店,她去取了一早就定好的蛋糕。
一切都和她预想的一样。
只是,当她提着蛋糕回家,公寓里空无一人。
楼上楼下都没有人。
她一间间房去找。
“薛裴?”
没有任何回应。
她开始慌张。
直到推开卧室的门,桌面上有一封信,还有一份合同,是房屋转让协议。
信件不长,还没看完,她的眼泪已经沿着脸颊滴在纸张上,氤氲出大片的墨色。
不知想到什么,她把chuáng头的抽屉拉开。
果然,里面放着三瓶已经开封过的药。
这段时间,他又开始服用药物了,但他从未和她提起过。
她所看见的薛裴,仍旧温柔体贴,和往常没有任何不同。
他隐藏得很好,不想让她知道。
薛裴的电话没打通,她立刻跑下楼,买了下一趟去海城的高铁票。
从北城到海城要两个小时,在去往海城的列车上,她反复看着这封已经被捏得皱巴巴的信。
“展信悦,
依依,当我给你写下这封信时,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你最爱的那档综艺节目,粥粥窝在你怀里睡得香甜,如果幸福有具体可感的图像,那应该就是这一刻。
前几天,我看了一本书,上面说:所谓jīng神失常,就是一再重复做同样的事,却期望有不同的结果。
这两年来,我好像都在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我想让你爱我,但却把你推得越来越远。
从今年的第一天开始,每一天我都在倒数,倒数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
一直以来,我都抱着最后的希望,从未想过放弃,直到李昼的事情发生,直到我多年前的谎言被戳破,我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人总要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
所以,后来我想,我人生里细微的每一步,以为无关紧要的每一个举动,其实都在不断错过你。
而你爱的那个少年时代的薛裴,也早已失去了所有的光环,成为了一个自私的懦夫,成为一个不敢面对现实的人。
原谅我没有勇气和你告别,所以我去了海城,打算休息几日,这套公寓留给你,我的衣物你随时可以清理,但那条围巾可以转寄给我吗?”
……
列车外的风景在急速后退,就像飞快掠过的旧日记忆。
那些快乐的,悲伤的,值得铭记的,和不忍回首的。
她想起老家的旧式DV机里还留着一段幼年时的影像,像素极低的画面里,她穿着粉色的公主裙追着薛裴到处跑,客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吴秀珍和薛阿姨在旁边满眼慈爱地望着他们,生怕他们摔着。
她还想起了无数个燥热的夏天,薛裴骑自行车载着同样穿着校服的她,穿过桐城的大街小巷,少年的衣衫永远都那样洁白,被风chuī得簌簌作响。
这两个小时,她几乎将过往的所有都回忆了一遍,病chuáng里苍白着脸色的他,发着烧也要赶过来的他,冬天帮她暖手的他……
记忆最后定格在两周前,她第二天一早起chuáng看到薛裴睡在客厅的沙发,她问为什么,他说“超过九点回家,所以只能睡在客厅了”,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高铁到站,她坐车去了海边。
不知道为什么,冥冥中她有一种预感,薛裴会在这。
笃定到她甚至没有打电话去确认。
跨年夜的海边,没有白天热闹,只有零星几个人。
隔着遥远的距离,她看到有个人坐在海边喝酒,那么冷的天,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是融入夜晚的黑色,旁边放着几个酒瓶,他望向波光粼粼的海面,月光下剪影落寞。
薛裴是第三次来到这片海。
第一次是他自己一个人来的,第二次是和朱依依一起来的,第三次又只有他一个人。
他坐在这里看着日落月升,静静地等待着这个夜晚的过去。
当海làng的拍打声里夹杂了熟悉的脚步声,薛裴终于回过头来。
风还在呼呼地chuī着,但他觉得此刻的时间仿佛静止了。
黯淡无光的眼睛重新有了光彩。
有人在夜色中向他走来,带着他所有的渴望。
“你怎么来了?”
她在他旁边坐下,他看到她手里还拿着他留下来的信。
他听见她说:“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薛裴确实是一个懦夫。”
心急速地往下沉,薛裴局促地收回视线,望向海面。
“因为,你连问我要不要继续走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夜很安静,薛裴握紧了手中的酒瓶。
朱依依缓缓补充了后半句,“如果,我说我愿意呢?”
薛裴的内心被一阵巨大的狂喜所充斥,立刻转过头,激动之下,声音都在颤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