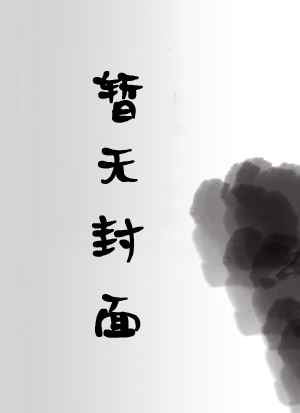喝没几杯,那侍女果然端了一个口径约莫一尺的大海碗上来,冯谖道谢接过,把那些残羹剩菜一股脑全倒了进去,这才拿起箸插在里面一通乱搅,约摸着搅匀了,依旧是呼噜呼噜一通狂吃。
别人一顿宴席要吃将近一个时辰,他倒好,三刻时间解决问题,这一下是吃了饱足。冯谖跟他师父一样食肠宽大,还有不拘礼节,反正是除了喝酒没他师父那么厉害外,其他各种不良嗜好学了个十成十。
现在的冯谖就是这样,**双腿,身子往后仰着,一只手支地,一只手在胸口上挠着。衣服因为把腰带——也就是那根破麻绳除下来了,所以敞开着,除了露出宽阔的胸膛外,还有那条犊鼻裈也是一览无余。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尴尬的时候,田文却笑了,道:“冯先生洒脱,我们都自叹不如啊!来来来,请满饮一杯!”
冯谖道声“多谢”,坐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对主人举杯,一饮而尽。
田文又道:“冯先生这般洒脱,必定是风尘异人,可否展露阁下绝学,给大伙一观?”
冯谖笑道:“公子说笑了,我之前便说过我这人除了力气略大,就只剩下吃饭了,如今诸位不都见到了么?”
田文认定了冯谖行为脱俗,定有勇略,正要再说些什么,就听到大厅外面吵嚷起来道:“哼!咱们也算是跟着公子许久了,居然让老子坐在外面!这他妈的是礼贤下士?”
田文眉头微皱,问道:“何人吵闹?”
不久一个家丁便道:“公子,是徐大海。他因为有人遮挡了烛光,看不清案上的酒菜,就说……就说……”
田文道:“但说无妨,不须顾虑。”
家丁咽了两口唾沫,才接着道:“徐大海说公子枉自说什么一视同仁,却搞得吃食都不相同,还故意找人遮掩了灯光,整个……整个……整个欺世盗名之辈……”
厅上坐的人都勃然大怒起来,纷纷叫道:“好个徐大海!居然敢这般侮辱公子,走!去收拾他去!”
田文道:
“大家慢着,你且说下去!”
家丁道:“他还说公子排餐,他坐廊下,这算是什么待客之道?”
田文挥了挥手,再一次制止了门下食客的行动,皱了皱眉道:“你去带他进来。”说完起身,亲自下阶等候。
不过片刻,门外走进来一个长的五大三粗的粗俗汉子,满脸怒气,一语不发。
田文道:“徐兄弟因何生气啊?”
徐大海道:“我随公子三年,一向敬服公子仁义,不想公子竟如此待我。岂不叫人心生怨恨?”
田文笑道:“不知在下哪里怠慢了徐兄?田文先在这里陪个不是,但还是希望徐兄言明,在下也好改正。”
徐大海哼了一声,道:“咱们门客不少,私下里分作三六九等也还罢了!这如今聚会宴饮的时节却还要弄花花肠子。田文,你莫以为找个人挡了灯光,我便不知道了。你这叫做欲盖弥彰,做贼的心虚吧!”
厅下门客都震怒道:“徐大海!放你娘的狗屁!”
徐大海一个粗人,反正也是豁出去了,对众人怒斥全然不放在心上,圆睁了双眼,接着怒道:“还有!凭什么要我坐在院子里?田文,你要不给我给说法,咱今天跟你没完!”
门外有门客离席进入,叫道:“徐大海!你既然来了三年,便也该知道,公子养士三千,人数何其之多?这间厅堂才多大?能坐得下这许多人么?你说你廊下院子里坐,难道我们就不是么?徐大海,做人讲良心,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徐大海道:“讲什么良心!他给我的饭食不好,故意找人遮掩了烛光,就是不愿意我发觉。我知道,我不过就是一个下等的门客,挑粪劈柴的出身,餐食难继,来投奔公子,公子收留,不至冻饿,我徐大海很是感激。但今天大伙欢聚,却拿些次等的东西与我,这算什么?恶心人么?田文!你这般做,不怕寒了兄弟们的心么?”
田文叹了口气,上前执其手,笑道:“原来事情根节在此,徐兄请随我来。”当下领了徐大海直上台阶,道:“徐兄若不嫌弃,我
的这些吃食与徐兄换换也不妨事的。”
徐大海定睛一瞧,阶上主座明明白白摆着一鼎丰肉,一只熟鸡,一尾鱼,一盘蔬菜与自己无异,面上一阵青一阵白的好不尴尬。
田文笑了笑道:“至于徐兄私下,在下亦可以以上宾之礼相待,还请徐兄息怒。可否?”
徐大海脸色发白,急忙退下跪倒,顿首泣道:“全是小人的过错,是小人以己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公子将我们分作三六九等,也是好的,我们这些下等的门客,身无一技之长,又不能为公子谋划政事,实在不敢巴望能得到多少好处,只要有一饭果腹足矣。进犯小人不长眼,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还诬公子不公正,小人实在羞愧难当!”
他说着站起了身来,环顾四周,也就冯谖离他最近,几步抢到冯谖跟前,一把抄起宝剑,面对田文道:“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我今天污蔑公子,已是无可挽回唯有,以死谢罪了!”说完,举剑就往自己脖子上刎去。
众人都大吃一惊,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