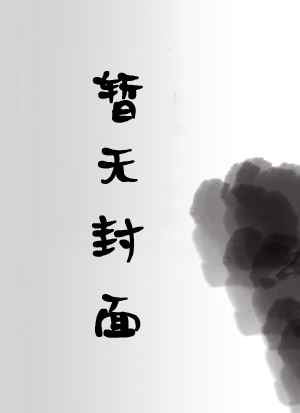聂浮潇不愿看她的眼睛,倒不是怕心软,而是兰歌的眼底里除了伤心,还有一丝狡黠。这个滑头滑脑的姑娘,谁知道她的控诉是出于真心还是苦肉计。他转身向外走,边走边说:“天境派不会留你的。”
兰歌捏紧了拳头。
聂浮潇走出门外,看到赵自洒伏在门后偷听。一见到他,赵自洒尴尬地叫了一声:“掌门师兄。”
“嗯。”聂浮潇冷淡地应了一声,继续走他的路。
赵自洒看着里面的兰歌气恼地一屁股坐下,不停往嘴里灌水,忽然下定了决心似的追上聂浮潇,叫道:“师兄,我有话说。”
聂浮潇却仿佛松了口气,回头浅笑,道:“你终于肯说了。”
闻言,赵自洒吃惊地说:“师兄,原来你早知道了?”
聂浮潇说:“救下兰歌以后,所有人都在笑,你虽然也笑,却十分勉强,我便知道,一定是你搞的鬼。”
赵自洒扁扁嘴,惊叹于聂浮潇惊人的观察力,又说:“我看不过去,一个姑娘家成天钱啊命啊的,对比步媱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底下,我就想给她个教训,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嗜财如命,没想到我偷偷隔空抹去了禁制,那饕兽喷火的速度会那么快那么猛。”
“饕兽本就积攒了数日的怨念,一旦解除禁制它势必会变得更加暴戾,更何况,兰歌虽然言行举止为你我所看不惯,到底是清白人家的孩子,不能拿她的性命开玩笑。”聂浮潇教导道。
“是。”赵自洒无精打采地应是,随后小心翼翼地问,“那师兄,你还会赶她走吗?”呐,这话他可不是因为同情兰歌以后的遭遇说的,而是觉得用这种手段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赶下山,不是他赵自洒的风格。
“以她的脾性,你觉得她会乖乖走吗?”聂浮潇留下了一句意味不明的话后,低笑着离去。
赵自洒一拍手,才知道被他的掌门师兄套路了,那话根本是对他说的!“这个师兄!”赵自洒忍不住一笑,高喊“等等我”追随而去。
果如聂浮潇所料,兰歌即便伤好了也死赖在天境山上,她平时都是活蹦乱跳的,一看到聂浮潇就假装瘸子,假装肚子痛,假装头疼脑热,假装腰酸,假装这也不舒服那也不爽快,总之是费尽了心思。
“哎哟,哎哟……”一日又碰到聂浮潇,兰歌照例抱着肚子惨叫。
封承欢在一边配合地问:“兰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很痛很痛很痛?”他一边偷瞄聂浮潇,一边加重语气强调。
兰歌叹了口气,扶着封承欢的小肩膀,说:“很痛,承欢啊,怕你兰姐姐,是过不了这个坎了,要是我有个什么一二三四五长短的,记得把我埋在后山,每年四月初的时候,来看看我……”说到动情处,还浮夸地抹了两滴泪。见封承欢发呆,她猛地掐了掐他小腰。
封承欢惊醒,继续配合演戏,硬挤出痛苦扭曲的表情来,说:“兰姐姐啊,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来看你的,我会带你最爱吃的东西来看你的。”
这入戏太深的两人抱头痛哭。
聂浮潇视若无睹,绕过他们自行离去。看来得找时间跟步媱谈谈心,看怎么管束承欢,不能任由他再跟着兰歌胡闹了。
“哈哈哈哈……”见聂浮潇果真没有提起赶她下山之事,兰歌和封承欢互击了手掌,捧腹大笑。
“哎,其实你这掌门师兄也挺笨的嘛。”兰歌说。
封承欢附和着点头,“以前没发现,现在我也觉得,掌门师兄确实挺笨的,这都看不出来,以后等他发现了,他肯定懊悔死了。”
兰歌窃喜。
“兰姐姐,我们今天玩什么?”封承欢整个人挂在兰歌身上,期待地问。
兰歌捏着下巴苦思,“我们这几天把山上的人都捉弄过了,连大厨菜叔的大黄也没放过,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这段时间,兰歌和封承欢天天腻在一起,一个不拘小节的混子,一个尚且年幼的顽童,两个人把兰歌以前整村民的那一套玩了个遍,开始封承欢还有些忸怩,后来见真的好玩,便放开了胆子,最重要的是,那些门众碍于一个是掌门带上山的,一个是掌门的五师弟,都不敢告状,只能打碎牙和血吞。不过兰歌的玩笑并不伤大雅,大多数时候,那些门众还是很喜欢兰歌的,他们在山上从来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兰歌还会讲故事给他们听,那些故事荒诞无稽,但配上兰歌的神态动作每每都能引得他们爆笑不止。
“对了兰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封承欢凑到兰歌耳边神神秘秘地说,“我姐姐喜欢三师兄。”
“小屁孩。”听完,兰歌睨了他一眼,“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我当然知道了。”封承欢不服气地说,“就是……三师兄像是山下的糖人,姐姐很喜欢吃糖人,就……就很想吃三师兄……不对,就看着三师兄都会流口水。”
兰歌一想,也对,她就很喜欢吃糖葫芦,可惜夫子小气,只在过年节的时候才肯买一串给她。“承欢啊,你说的秘密也不好玩,你姐姐喜欢三师兄,跟我们也没关系,还不如发呆呢。”她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
封承欢紧挨着她坐下,双手撑着脑袋,无聊得直